1724年,岳钟琪下令斩了6000名喇嘛,寺庙烧成灰,岳钟琪没眨一下眼。他算过账:清军死了一半,粮食只够三天,如果留着6000张嘴,明天就没有粮食,随时会反噬。 1724年的青海高原,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光秃秃的山丘。 清军大营里,岳钟琪盯着粮草账簿,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账上的数字让人心惊:军粮只够吃三天了,而麾下将士已经折损近半。 半个月前,清军与罗卜藏丹津的叛军在柴达木盆地血战。虽然赢了,但代价惨重。现在部队带着六千多名俘虏——大多是喇嘛和寺院僧兵,被困在这荒凉之地。后方的补给线被叛军残部切断,大雪封山,援军一时半会儿根本到不了。 岳钟琪走出大帐,望着远处黑压压的俘虏营。那些喇嘛穿着绛红色僧袍,在寒风中缩成一团。看守的士兵们眼神警惕,握着刀柄的手冻得发紫。有几个伤兵靠在帐篷边,裹着带血的绷带,眼神空洞地望着天空。 “大将军,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副将哈元生凑过来,胡茬上结着冰碴,“咱们的人快撑不住了,粮食再这么分下去,谁都活不成。昨天又死了十几个伤员,都是饿死的。” 岳钟琪没说话。他何尝不知道?六千俘虏,就是六千张嘴。每人每天就算只吃半斤粮,一天也要消耗三千斤。而军中的存粮,满打满算不过万斤。他走到伤员帐篷里,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兵正在发烧说胡话,嘴里不停地喊着“娘”。军医摇摇头:“没药了,粮食也不够,怕是撑不过今晚。” 回到大帐,岳钟琪把算盘打得噼啪响。亲兵端来的晚饭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粥,配着干硬的烙饼。将士们已经吃了三天这样的伙食。帐外传来士兵的抱怨声:“当兵的吃不饱,俘虏倒还能分到口粮...” 深夜,几个将领聚在帐中。有人提议放掉俘虏,立即遭到反驳:“放他们走?转头就会带着叛军杀回来!咱们现在这个状况,经不起再次袭击了。”有人建议分粮,话没说完自己先摇头——粮食根本不够分。 哈元生猛地站起来:“大将军,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再这样下去,咱们全军都得饿死在这里!” 岳钟琪盯着跳动的烛火,想起出征前雍正皇帝的嘱托:“西北安危,系于将军一身。”想起战死的将士,想起还在苦等的援军。最后想起粮官报来的数字:三天。 他闭上眼,仿佛看到全军因断粮而溃散的场面,看到叛军卷土重来,看到西北再度陷入战火。 第二天清晨,岳钟琪下令将俘虏分批押往山谷。许多喇嘛以为要释放他们,甚至有人合十致谢。直到看见士兵们亮出刀剑,才意识到要大祸临头。 屠杀持续了一整天。山谷里的惨叫声久久不散,鲜血染红了积雪。有些士兵边哭边挥刀,有个年轻士兵砍到一半突然扔掉刀,跪在地上呕吐不止。岳钟琪全程站在高处看着,面无表情,但握剑的手捏得发白。 随后他下令烧毁附近的寺庙。火焰腾空而起,经卷、唐卡、佛像在火中噼啪作响。有老喇嘛哭喊着扑向火堆,被士兵死死拉住。浓烟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和血腥气。 “为什么连寺庙都不放过?”年轻的文书忍不住问,声音发抖。 岳钟琪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这些寺庙是叛军的据点,喇嘛是他们的兵源。今天不除根,明天就有更多人披上僧袍拿起刀。我们输不起第二次了。” 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有人弹劾岳钟琪滥杀,雍正却力排众议:“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但私下传给岳钟琪的密旨里,皇帝还是提醒他“慎行”。 很多年后,岳钟琪已经退休回乡。有次醉酒后,他对老部下说:“那六千条人命,我每晚都数得清。有时半夜惊醒,总觉得手上有洗不干净的血腥味。”他一生征战无数,唯独这一仗,从不让人立碑纪念。 活下来的士兵们很少提起那天的事。有人终身吃素,有人常年礼佛。哈元生后来官至提督,每次路过青海都要绕道而行——他说总能听见山谷里的风声像哭声。当年那个呕吐的年轻士兵退伍后出了家,据说常在佛前长跪不起。 活佛的预言没有应验,岳钟琪活了七十多岁。但有人说看到他晚年经常独自发呆,有一次大雪天竟光着脚在院子里站了一夜,任家人怎么劝都不肯进屋。 岳钟琪的做法,确实保证了清军主力等到了援军,最终平定了叛乱。雍正皇帝在奏折上批了“不得已”三字,这大概是对那六千亡魂唯一的评价。西北确实获得了十余年的太平,直到乾隆年间才再次动荡。 历史总是这样,一边记载着“不得已”的抉择,一边掩埋了雪地里的血色。岳钟琪的账算得很清楚:用六千条命换来了西北十年太平。只是不知道他晚年数着那些人命时,算的又是什么账。 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曾经诵经礼佛的生命,都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永远留在了青海的山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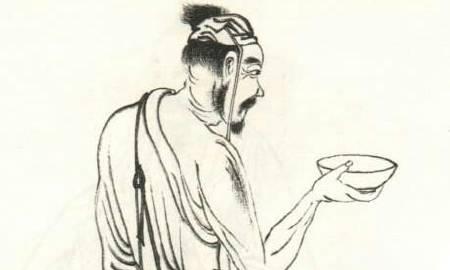





wlqcq
我敢说,如果岳将军不杀,后面那些红袍子,绝对会再叛
致敬乌雅兆惠
没出息。学学乌雅兆惠,阿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