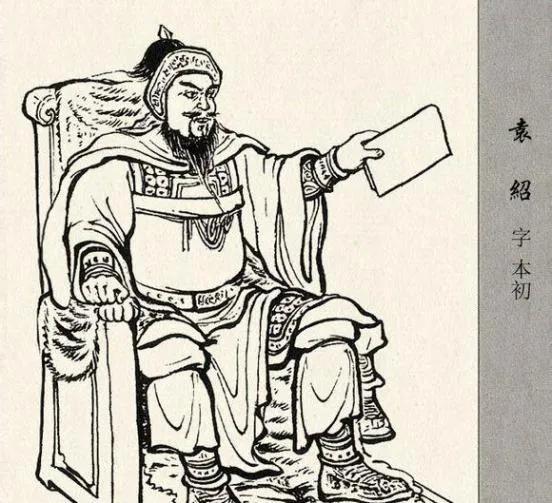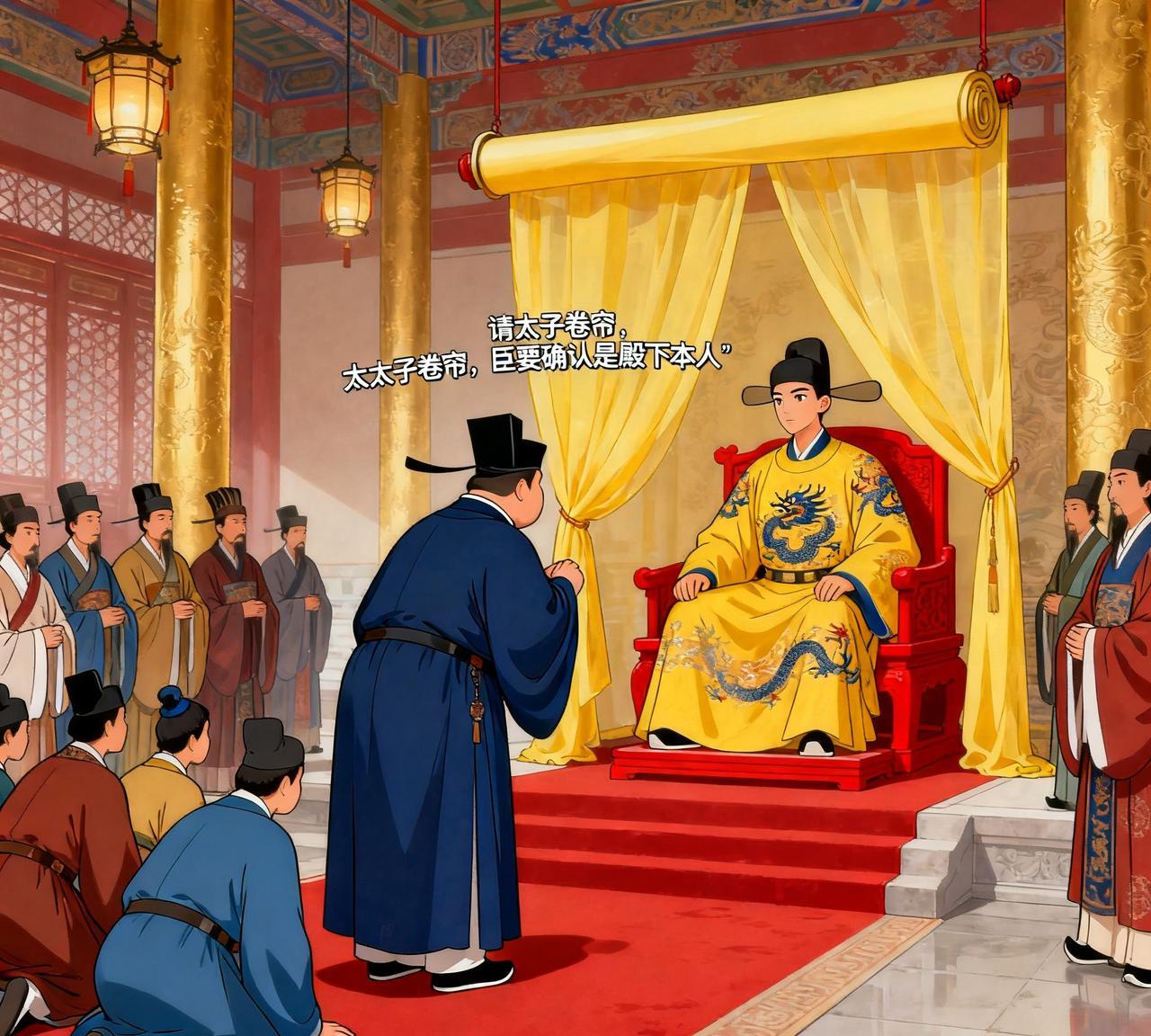559年,34岁的高洋如厕时不慎掉进粪坑,被人从粪坑里捞上来后,奄奄一息的他死死攥住弟弟高演的手,双眼含泪:“我死后,皇位你可以夺走,但不要杀我的儿子。” 邺城宫殿的地砖还沾着未擦净的秽物,高洋咳出的血沫子溅在高演的明黄蟒袍上,像极了他当年亲手杀死的那只白狐留下的爪印。高演看着兄长浮肿的脸,想起十年前那个在晋阳起兵的少年——那时的高洋总爱跟在自己身后,抢着背最重的铠甲,说“二哥,等我当了皇帝,让你当兵马大元帅”。 “陛下放心。”高演掰开他的手指,指尖沾着股挥之不去的臭味,“太子是高家血脉,臣会护他周全。” 高洋的眼睛亮了亮,忽然抓住床沿剧烈咳嗽起来。太监递上的帕子很快被染红,他指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响声。高演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想起去年夏天,高洋把太子高殷架在脖子上摘槐花,笑得像个傻子——那时的皇帝,还没疯到往大臣肚子里灌水银,还没把宠妃的骨头做成琵琶。 三天后,高洋断了气。临死前他攥着高殷的小手,把一块刻着“齐”字的玉牌塞进孩子掌心,血手印在玉上洇开,像朵丑陋的花。 太子登基那天,高演站在阶下看着侄儿发抖的背影。满朝文武都知道这孩子撑不了多久——高洋在位时杀了太多宗室,那些人正等着找个由头把小皇帝拉下马。果然不出半年,有个老臣在朝堂上哭诉,说太子偷偷学汉人的礼仪,是想忘了鲜卑祖宗。高演没说话,只是把那本被太子翻烂的《论语》扔在地上。 夜里,高演去东宫看高殷。孩子正对着一幅画像发呆,画上的高洋穿着龙袍,眼神却像头困兽。“二叔,”高殷怯生生地递过一块点心,“这是御膳房新做的,爹以前最爱吃。” 高演的心猛地一揪。他想起母亲娄太后的话:“你哥疯了一辈子,难道要让他儿子也落个被人砍头的下场?”那天他在祠堂跪了整夜,高洋的牌位前积着层薄灰,像极了他掉进粪坑那天的狼狈模样。 政变来得比想象中快。高演带兵冲进皇宫时,高殷正坐在地上拼积木,那些木头块被他摆成宫殿的样子,缺了个角的“龙椅”旁放着那块带血的玉牌。“二叔要抢我的皇位吗?”孩子仰起脸,眼里没有恐惧,只有茫然。 高演把他抱进偏殿,指着窗外的老槐树:“你爹小时候爬树摔断过腿,太医说可能站不起来,他硬是拄着拐杖练了三个月。”高殷的眼睛亮了亮,伸手去摸高演腰上的佩剑——那是高洋当年送他的礼物,剑鞘上刻着兄弟俩的名字。 被废黜的太子被封为济南王,送往晋阳居住。高演去送行时,见高殷的包袱里裹着那本《论语》,还有块没吃完的点心。“二叔记得答应过爹的话吗?”孩子拉着他的衣角,小手冰凉。 高演没回答。他看着马车消失在尘土里,忽然想起高洋临死前的眼神——那里面有恐惧,有哀求,还有种说不清的解脱。或许那个疯皇帝早就知道,在这个弑父杀兄成了家常便饭的王朝,活着比当皇帝更难。 一年后,娄太后派人送来一壶毒酒。高演盯着酒壶上的缠枝纹,想起高殷刚学会写“高”字时,把最后一笔拖得老长,说“这样才能把高家撑住”。他把毒酒倒进院子里的石榴花下,花瓣很快蔫了,像被血浸透的样子。 可该来的终究躲不过。有天夜里,高演梦见高洋浑身是粪水地站在床边,举着那把琵琶说:“你看,这弦断了。”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攥着高殷的玉牌,指节都捏白了。没过多久,晋阳传来消息,济南王“暴病身亡”,死时手里还攥着半块发霉的点心。 高演没哭。他在高洋的牌位前坐了三天,把那块玉牌放在兄长灵前,上面的血印早就干了,像道永远洗不掉的疤。有个老太监说,夜里听见祠堂里有哭声,像个孩子在喊“爹”,又像个男人在说“我错了”。 三年后,高演骑马时摔断了腿,跟当年的高洋一模一样。弥留之际,他看着儿子高百年,忽然想起那块带血的玉牌。“别学你大伯,也别学我。”他气若游丝,“做个普通人,守着槐树过日子就好。” 可这乱世容不得普通人。高演死后没多久,他的儿子也被人杀了,死时才七岁。 邺城的老槐树还活着,每年夏天都开得满树雪白。有路过的老人说,夜里能看见两个穿龙袍的影子在树下说话,一个哭,一个叹气,风吹过的时候,能闻见股说不清的味道,像槐花的甜,又像粪坑的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