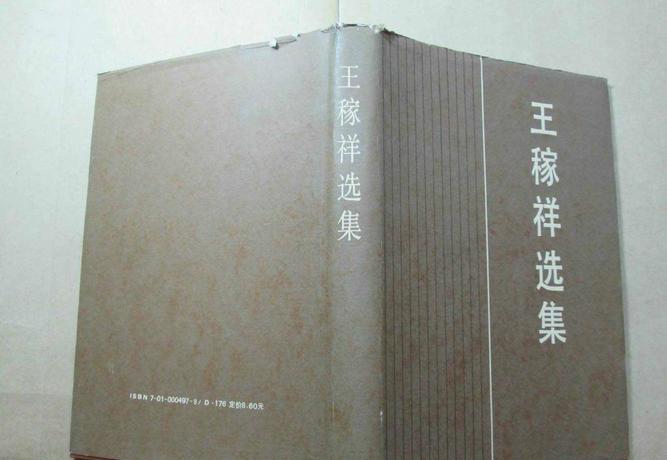1983年,朱德元帅的孙子被执行枪决的第二天,他的夫人康克清正常外出工作,上班路上,她平静地对司机说:“刘师傅,我孙子犯了罪,昨天被枪毙了。” 1983年的天津,秋风走得急。 沿海的风总是带着点盐腥味,拐过街角,吹乱行人的发,也钻进宽松的旧夹克里。 那时的早晨,电车叮叮当当,街边的早点摊还冒着热气,谁也没想到,就在这座城市里,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将走到人生的尽头。 他姓朱,朱国华。 名字听起来普通,可一旦有人提到他的家世,空气会短暂地凝固几秒——他的爷爷,是朱德。 朱德年轻时打过仗,晚年掌握过兵权,身上的军装一穿就是几十年。 可这人偏偏有股倔劲儿,连国家发的元帅津贴都不要,说自己已经领了工资,不能多拿。 家里人多,开销紧,可他照样不松口。 对待孩子也是一样,疼是疼,但规矩一点不少——书要好好念,做人要清白,别想着走捷径。 小时候的朱国华,很像一块被雕得端正的木料。 老师说他懂事,邻居夸他安静,成绩在班上不算拔尖,但也够得上“有出息”的样子。 只是日子总会在某个瞬间转向。 1974年,他的父亲病逝。 两年后,朱德也走了。 两根压在家里梁上的柱子,一下塌了。 康克清忙于工作,来不及照看这个刚成年的孙子。 1976年,朱国华毕业,被分配到天津铁路局。那时的天津,港口货轮进出,街上能听到南腔北调,他在这里安顿下来,起初一切看似平稳。 可人一旦离开了那双盯着的眼睛,就像风筝断了线。 铁路局的活不算重,他遇到了一些“懂人情”的同事和朋友,笑脸送到他眼前,桌上摆着好酒好菜,夜里带他去看霓虹闪烁的地方。 年轻人很容易被这种热闹裹挟——尤其是知道自己姓什么、爷爷是谁的时候。 他开始旷工。 领导找他谈,他笑笑,不吭声。 他心里明白,大不了批评几句,不会真有事。 没多久,这种放松就滑向了另一头。 他结识的那些人,手段脏得很,酒过三巡,话里夹着暗示,教他怎么“玩得痛快”。 第一次,他盯上了两个年轻姑娘。 对方并不买账,他就找借口把人约到自己住处。 几个狐朋狗友早在屋里等着,那天发生的事,不必多说。 姑娘离开时低着头,既怕名声,也怕他的背景。 沉默,成了他的护身符。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他的胆子越养越肥,出手越来越狠。 强奸、猥亵、威胁,手段翻着花样来。 有人算过账,被害人总数超过八十人。 这在当时,像一块沉石,压得人透不过气。 1982年秋天,天津的天灰得很快,傍晚就像有人拉了帘。 公安接到举报,开始暗中摸查。 他以为这只是个小插曲,自己背后站着的名字够硬,不会真翻船。 十月,警察出现在他面前,那一刻,他的神色据说还带着点不屑。 1983年的“严打”风声已经很紧。 中央下令,对严重刑事犯罪从快从重处理,社会治安要立刻见效。 朱国华的案子被提上日程,卷宗很厚,指控一条条列着。 天津法院的判决干脆利落——死刑。 上报中央,批复执行。 那年的九月,风大得能把宣判大会上挂的布条吹得猎猎作响。 天津人民体育馆里,人头涌动,谁都想看看这个站在被告席上的年轻人。 喧哗声里,有人低声说:“真是他。” 也有人嘀咕:“不会开枪吧?” 可队伍很快拉走了他,押上了车。 刑场外,土路还带着昨夜的潮气。 执行队列整齐站好,几个动作之间,一声枪响,像钉子钉进木板。 二十五岁,一个姓朱的年轻人倒在地上。 有人说,现场风很凉,吹得人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案子过后,坊间传出各种版本的故事。 有的说康克清在死刑报告上写了“同意死刑”,也有人说她全程没插手。 真实与否已难辨,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为他挡下这颗子弹。 这件事让很多人意识到,那种“出身好就能免灾”的想法,在这里失了准。 这桩案子后来成了八十年代严打的标志之一。 报纸、茶馆、胡同口,都有人谈起它,不只是因为罪行恶劣,也因为它打破了某种想象。 更隐秘的,是它在法律界留下的涟漪——那时的“流氓罪”,从街头斗殴到性侵,都能往里装。 这个口袋罪后来在1997年被废掉,算是给历史留下一道注脚。 秋天很快过去,风里开始带着冬天的冷。 街边卖糖炒栗子的炉子冒着热气,天津港的船笛声在雾里传得很远。 人群散去,宣判大会的横幅早被收起,体育馆外的地面上,还留着几个鞋底印,深浅不一,被风沙慢慢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