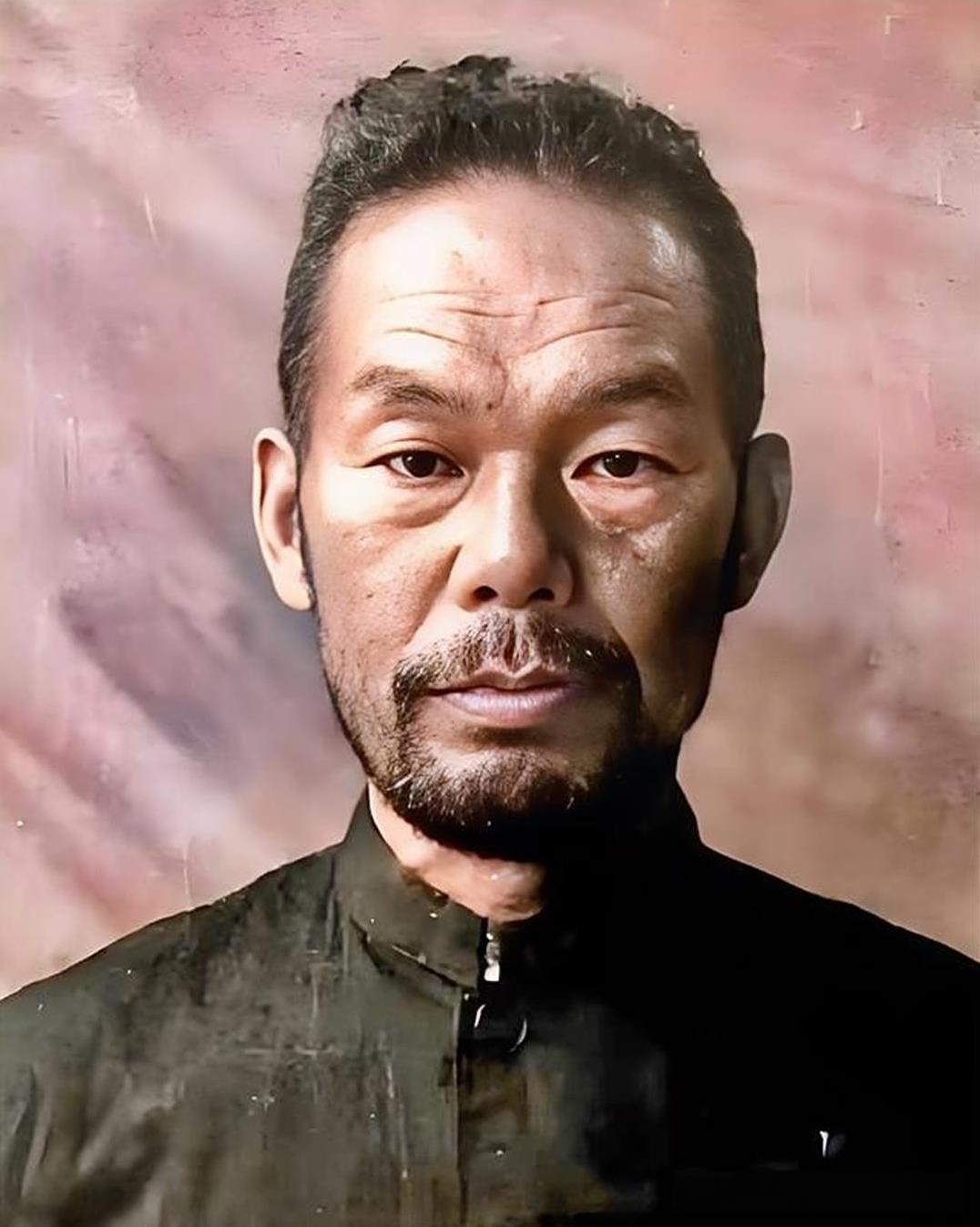1947年4月26日,南京雨花台,空气中压抑的气息让人屏住呼吸。那天,甲级战犯谷寿夫被押赴刑场。消息早已传遍南京,大批市民自发赶来。他们要亲眼见证刽子手的末路。枪声还未响起,人群已经沸腾。对无数在南京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这是等待十年的一刻。 押解车缓缓驶向刑场,铁链的摩擦声与脚步声交织。谷寿夫面色苍白,腿脚发软,几乎无法自己走下车。宪兵搀着他一步一步往前挪。人群隔着警戒线,目光像利剑般刺向他。没有人同情,没有人怜悯。所有人都在等待正义的子弹。雨花台的土坡上,刑场已经布置完毕。时针逼近,历史的清算即将落地。 这个人何以走到这一步?谷寿夫生于日本冈山县,出身军人世家,年轻时便投身军国主义扩张。他在日本陆军中一路升迁,积累战功,被视为“能征善战”的将领。但在中国,他的名字注定与屠杀相连。1937年冬天,他率第六师团攻入南京。在那场血色的浩劫中,数十万平民和战俘惨遭杀害,城市被化为人间地狱。他的命令,让刀光和火焰吞噬无辜。 南京大屠杀的惨状被无数史料记载。血泊遍地,尸体塞满江岸。教堂与难民区的记载揭露了系统性的屠杀与强奸。谷寿夫作为前线指挥,无法推卸责任。他不只是冷眼旁观者,而是直接的施暴者。他的师团实施大规模清剿,毫无区分对象,屠戮成性。幸存者的哭喊与日军档案,构成了最沉重的证据。 战败之后,谷寿夫并未立即落网。他被押回日本,关押在巢鸭监狱。随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各地审判陆续展开,他的罪行被逐步查清。1946年,他被引渡至南京。这座城市等待他多年,正义的法庭也早已准备好。南京军事法庭成立特别庭审组,将谷寿夫列为首批公审的甲级战犯。 庭审场面震撼。谷寿夫企图否认,坚称无罪。但铁证如山。目击证人站上证台,详细描述屠杀经过;法医学专家提交掩埋坑挖出的尸骨;历史影像和日军档案在庭上播放。六百余份检举与证言像潮水般涌向他,把所有抵赖淹没。面对这些,他沉默,眼神闪烁,已无力反驳。 1947年3月,军事法庭宣布判决。谷寿夫因屠杀战俘和平民罪行,被判处死刑。庭内一片肃静,判词铿锵有力。上诉无果,蒋中正批复维持原判。谷寿夫被正式定罪,等待的就是刑场。对南京百姓而言,这是迟来的正义。消息公布,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很多人表示要去亲眼见证刽子手伏法。 行刑前一夜,谷寿夫写下遗书,语气中满是恐惧。他明白自己再无生路。第二天上午,宪兵将他押出监牢。押解车一路经过人群,围观者沉默中透出冷厉。到达雨花台时,他已吓得站不稳。宪兵只能架着他走到刑场。雨花台春草青青,脚下却承载着沉重的记忆。 11时30分,行刑命令下达。宪兵班长洪二根举枪瞄准,扣动扳机。子弹从后脑射入,从口中穿出。谷寿夫应声倒地,尘埃飞起,血染黄土。现场数万市民爆发出掌声与呼喊。有人喜极而泣,有人举手击掌,声音传遍雨花台。那一刻,死难同胞似乎在阴间得知,刽子手终于受到了惩罚。 这次公审和行刑,不仅是对个人罪行的清算,更是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回应。数十万死者的亡灵,终于得到告慰。市民的掌声,不只是发泄愤怒,更是一次历史的宣告:无论过去多久,正义不会缺席。战争的罪行,必将得到惩处。 谷寿夫的伏法,也为后续的审判开了先河。在南京,还有多名战犯因大屠杀和战争暴行被追责。像向井敏明、田中军吉等,在其他审判中同样被判处死刑。一个个名字被载入史册,他们曾经不可一世,如今都成了正义的祭品。这一连串的判决,告诉世人:战争罪责不能逃避。 几十年后,南京雨花台和江东门等地建立起纪念碑和纪念馆。每年的悼念仪式,都会让人回忆那段血色历史。谷寿夫的名字,也在展板和档案中被反复提及。不是为了纪念他,而是提醒世人:历史的血债必须铭记。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 这段历史让人看到一种对比:一个昔日的侵略者,面对正义时惊恐失措,无法自控;而无数无辜的南京人,在屠刀下没有退路,承受了惨绝人寰的痛苦。这样的反差,正是正义与邪恶的对照。那颗子弹,击穿的不只是谷寿夫的头颅,也击碎了军国主义的傲慢。 今天回望,谷寿夫在雨花台的伏法,不仅是法律的胜利,也是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它让我们看到,历史不会遗忘,人民不会原谅。屠杀者逃不过审判,侵略者必被追责。南京城的春风中,埋藏着当年的呐喊与鲜血,也铭刻着正义必达的信念。 1947年4月26日这一天,雨花台见证了历史的一瞬间。枪声回荡在城头与山谷之间,震彻人心。无数人从这一刻起更加确信,正义可以迟到,但绝不会永远沉默。谷寿夫的末路,正是无数亡灵与幸存者等待的答案。


![思想殖民[无奈吐舌]](http://image.uczzd.cn/931608675135411061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