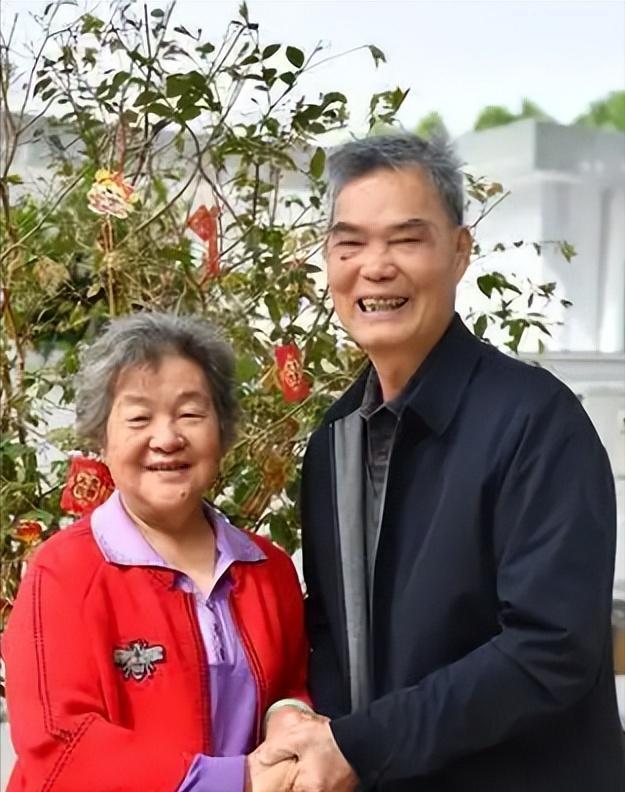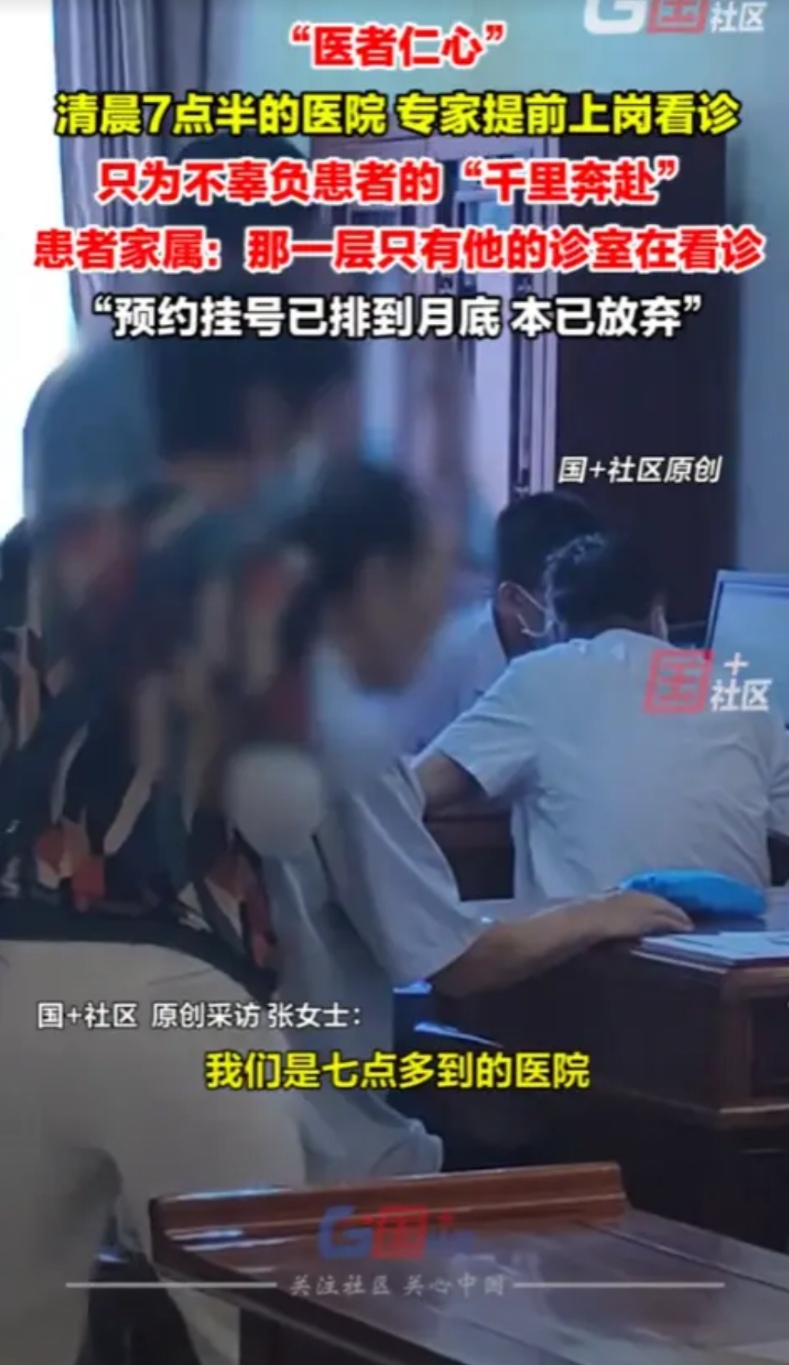1986年10月2日夜里,韩先楚突然口吐鲜血,最后一次病危。主任医生王梦薇立即赶来抢救,沉着地采取应急措施,年届古稀的赵东海教授也赶了过来。 当韩先楚又一次昏迷,两位医生一直守护在床边,直到第二天凌晨韩先楚溘然长逝。王主任累晕过去,等她醒来时愧疚地说,多么好的司令员啊,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救他。韩先楚得的是肝癌,华佗再世也束手无策。 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病榻上的韩先楚,此刻却显得格外平静。就在几天前,医生提议再做一次手术,他轻轻摆了摆手:“七十多岁的人了,别给国家添负担。”他特意请来了熟悉的理发师王春莲,花白的头发被一丝不苟地修剪整齐,仿佛即将出征的将军在整理仪容。 窗外,庆祝国庆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而病床上的他,只对家人留下了两句嘱托:不要插胃管,不要进八宝山——“送我回红安,我要和军长吴焕先在一起,和牺牲的战友们葬在一块儿。” 两年前,医生拿着肝癌晚期的诊断书,沉痛地告知“最多还有半年”。将军听完,脸上只是掠过一丝淡然的笑意:“枪林弹雨里死过多少回了,有啥好怕的?”这不是故作轻松。 战争年代,子弹曾擦着他的头顶飞过,削掉一块头骨,军医事后都后怕:“再高一丁点,神仙也难救!”更传奇的是长征路上,一颗哧哧冒烟的手榴弹,鬼使神差地从他衣服破洞钻进裤腰,竟然哑了火!这种九死一生的经历,锻造了他钢铁般的神经。 打仗时他信奉“只有先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当上师长、军长照样带头冲锋。打海南岛时,身为兵团副司令的他差点被炮弹击中,是被警卫员死死抱住硬塞进船舱才躲过一劫。 这份在战场上淬炼出的、近乎“不要命”的顽强,成了他与病魔抗争最有力的武器,硬是将半年的“最后通牒”延长到了两年。 为什么他如此执着地要回到红安?1981年那次回乡探访,或许藏着答案。车子刚驶进吴家嘴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拨开人群,颤声呼喊:“祖宝!”,这个阔别了七十年的乳名,瞬间击中了将军的心。 儿时的伙伴陈尊友挤上前,捶着他的肩膀半开玩笑半埋怨:“当了三十多年大官,咋还让我穿着草鞋受穷?”韩先楚嘴唇翕动,眼眶泛红,那一夜辗转难眠。 红安,这片土地承载了太多。十四万烈士的鲜血浸透了这里的黄土,走出了六十一位开国将军。六十年代饥荒肆虐,得知乡亲们啃树皮度日,他倾尽所有寄回了全家攒下的两百公斤粮票。 寒冬腊月,他调拨五万件军大衣给乡亲御寒,费用无处报销,他拄着拐杖斩钉截铁:“从我工资里扣!扣完我的扣我儿子的!”秘书回忆,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还常常念叨:“记得买些树苗回去,家乡的山,不能秃了啊……” 10月3日清晨,昏迷中的将军忽然清醒过来。他吃力地抬起手指,指向病房的衣柜。儿子立刻明白,捧出那套洗得发白却熨烫得笔挺的旧军装。 家人含着泪,一粒一粒为他系好纽扣,端端正正戴上军帽。他示意护士搀扶自己到镜前。镜中的人形容枯槁,脸色灰败,但那领章却依旧鲜红夺目。 他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站在定边城头,意气风发的模样。七点四十分,心电监护仪发出一声长长的悲鸣。 家人整理遗物时,抽屉里只有几本泛黄的笔记本、用皮筋捆扎整齐的几百元零钱,还有半袋早已失效的六十年代粮票,这就是一位开国上将的全部积蓄。 最令人动容的细节发生在临终前。当时他身上插着三根输液管,却用尽力气拨通了老战友余秋里的电话,声音微弱却清晰:“我的秘书姚科贵,跟了我二十年……别让他闲着。”追悼会上,跟了将军半辈子的姚科贵站在第一排,腰杆挺得笔直,强忍着泪水。 在许多人眼里,将军有时“不近人情”:大雨天,他会把自己的雨衣让给站岗的哨兵,自己冻得直哆嗦;警卫员心疼他胃不好,偷偷藏点饼干,他会“吼”起来:“仗是我一个人打的吗?!”非逼着大家分着吃。他总念叨:“当官的饿几顿有人管,小战士淋雨生病,谁看得见?” 他拒绝了八宝山的哀荣,最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红安。细雨霏霏中,故乡的乡亲们赤着脚,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里,迎接他们的“祖宝”回家。 松柏环绕的陵园里,他长眠在少年时照顾他的“秀姐”身旁,紧挨着长征路上为他挡下子弹牺牲的吴焕先军长。三十八年过去,海南岛战役的硝烟依然在历史课本中弥漫,而这位传奇的将军,终于枕着故乡温厚的黄土,获得了永恒的安息。 “生在红安,死也要回。”——韩先楚,1986 本文事实核查综合自《解放军报》专题报道及《韩先楚将军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