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7年,噶尔丹自杀,骨灰和女儿都被手下人献给了康熙。死前他曾绝望地感叹:“同样是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听说康熙走过的沙滩能涌出甘泉,石头能长出青草,这是天在助他!我部下都投奔他去了,这是人在帮他!可我该如何是好呢?”
康熙三十六年春,阿察阿穆塔台的寒风卷着骨灰般的雪粒,掠过噶尔丹腰间的鎏金转经筒。
这位曾让准噶尔铁骑踏遍天山的雄主,此刻正用藏刀削着最后半块风干牦牛肉。
刀刃划过皮革的沙沙声,与三丈外丹济拉磨箭镞的动静交织,在空荡的营帐里奏响末路挽歌。
十七年前在扎什伦布寺受戒的场景恍如昨日,四世班禅将金刚杵压在他肩头时,殿外十万信众的诵经声震落了经幡积雪。
彼时的转世活佛不会想到,二十年后自己会用这双结过法印的手,点燃乌兰布通草原上焚烧驼城的烈火。
昭莫多山麓的月光浸透断箭,映出噶尔丹甲胄上的双头鹰纹,这是沙俄特使五年前赠予的盟约信物。
当年戈洛文捧着《尼布楚条约》文本策马西去时,准噶尔斥候带回的密报还沾着贝加尔湖的潮气。
如今镶金羊皮卷早已霉变,就像喀尔喀草原上那些被清军炮火轰碎的盟誓。
篝火将熄的刹那,噶尔丹瞥见侍从怀中的《甘珠尔》经卷。
这部由八世达赖亲赐的藏文典籍,扉页还留着乌兰布通决战前夜的血指印。
彼时他蘸着阵亡将士的鲜血,在"众生平等"的经文旁批注战策,浑然不知千里外的紫禁城里,康熙正用朱笔圈定三路合围的杀局。
最后一匹战马倒毙时,噶尔丹在沙地上画出七政宝轮图。
指尖触到某处凹陷,竟挖出半枚顺治通宝。
这是二十年前征服叶尔羌汗国时,从波斯商队劫来的战利品。
钱币背面的满文"宝泉"二字,此刻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青灰,恍如当年在五台山行宫,顺治帝赐给年幼康熙的压胜钱。
丹济拉捧着骨灰坛走近时,噶尔丹正将最后三粒舍利子投入火堆。
这些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的头骨所炼圣物,在烈焰中爆出噼啪脆响。
1696年冬,正是这位喀尔喀贵族的叛变,让清军骑兵如天降神兵般穿透准噶尔防线。
火光映出噶尔丹嘴角苦笑,他终于明白为何密宗典籍说"业火焚身时,方见因果真"。
当清军前锋的马蹄声震落帐顶经幡,噶尔丹解下颈间九眼天珠。
这串由七世达赖加持的圣物,每颗玛瑙都嵌着微型转经轮。
他记得康熙三十三年冬,策妄阿拉布坦叛军攻陷伊犁时,正是靠这串天珠的指引,才带着三百亲卫穿越死亡沙漠。
如今转经轮卡死的嗡鸣,像极了昭莫多战场上哑火的俄制火枪。
骨灰坛嵌入黄沙的瞬间,戈壁突然刮起怪风。
丹济拉看见主帅的斗篷鼓成经幡,猎猎作响中隐约显出"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十三"的藏历符咒。
这个日期,恰是二十年前他在拉萨哲蚌寺算出"星坠狼居胥"的凶兆。
当第一捧骨灰随风飘向东方,远处清军龙旗已卷着沙暴逼近。
康熙抚摸着镶金骨灰坛时,御帐外的狼居胥山正落下百年未见的血月。
钦天监呈上的星象图显示,紫微垣旁新现的客星恰对应阿察阿穆塔台方位。
随驾的蒙古王公认出坛底焦痕,正是噶尔丹随身法器的莲花纹。
当年乌兰布通战场上,这朵金莲曾悬在准噶尔中军大纛,被清军红衣大炮轰成碎片。
班师途中,康熙特命在昭莫多战场旧址栽种胡杨。
二十年后,当策妄阿拉布坦之乱再起,这些树木的年轮里已嵌满箭簇铁屑。
暮年的帝王常对群臣说起,那夜狼居胥山的风中有转经筒的嗡鸣,而史官笔下"噶尔丹仰药自尽"的朱批,始终笼着大漠孤烟的迷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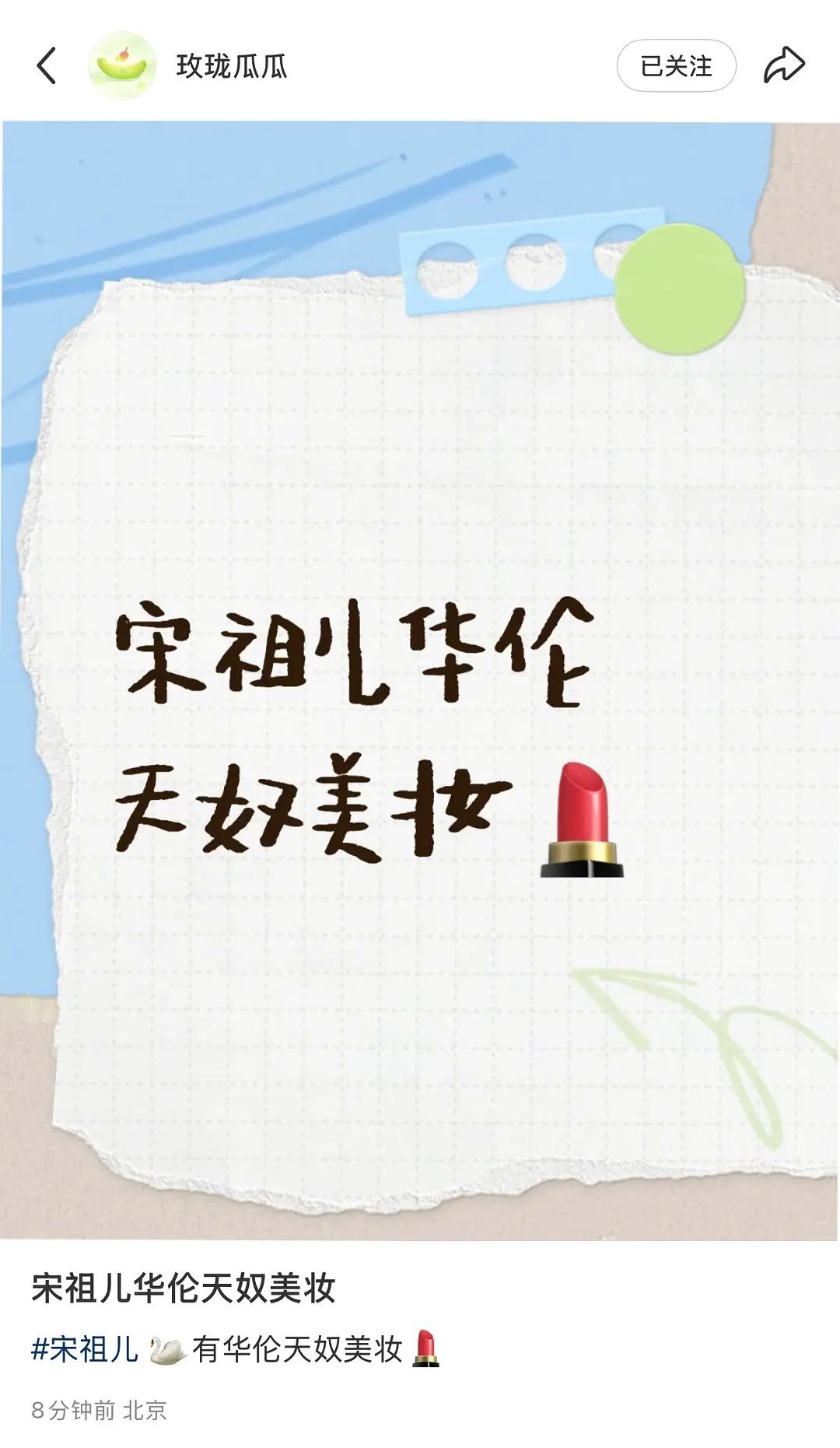







gjebr
都是鞑子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