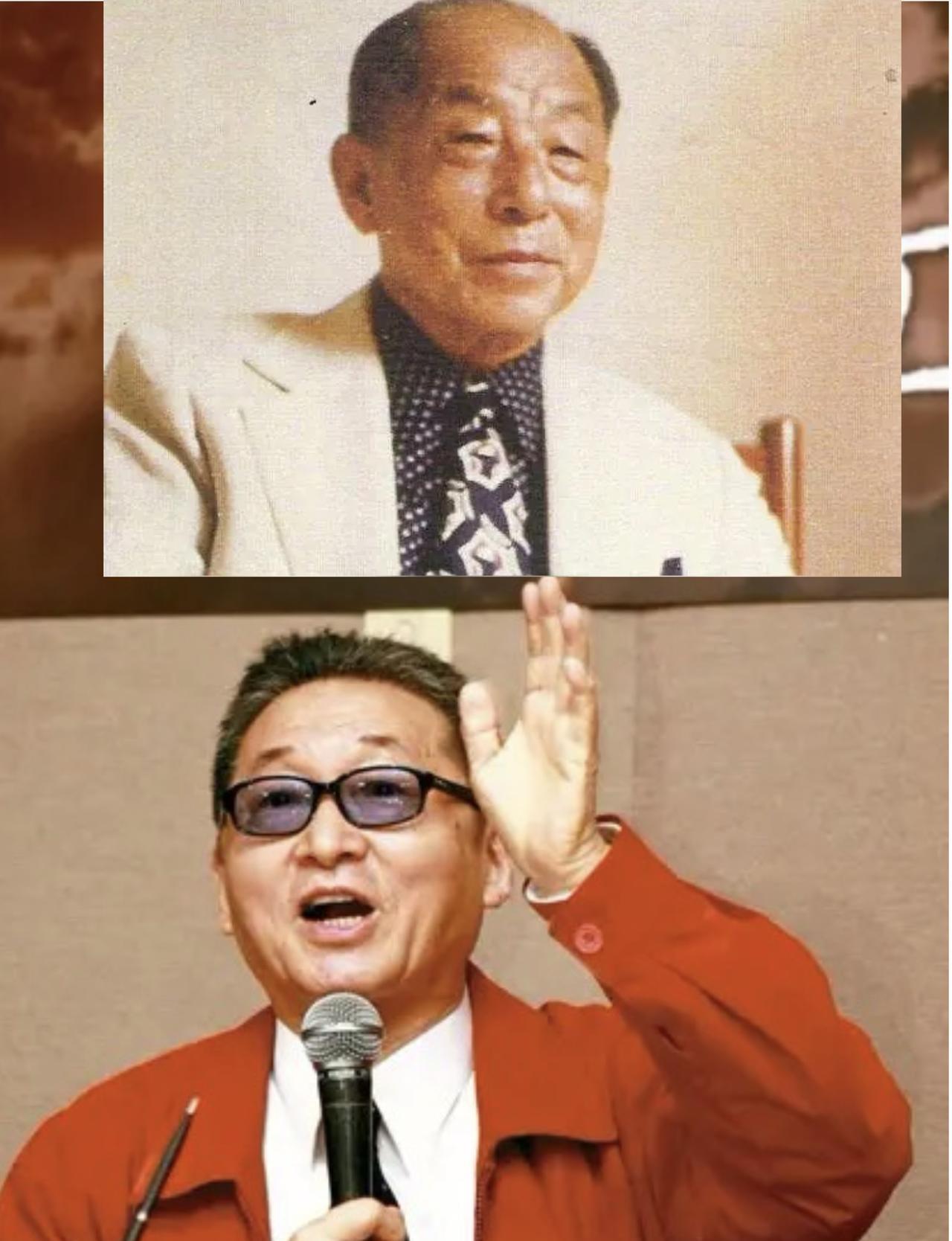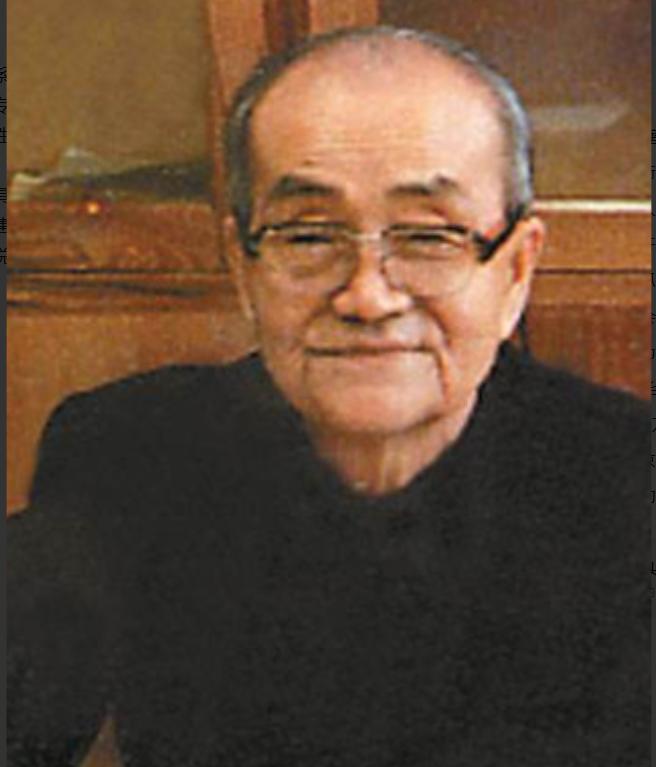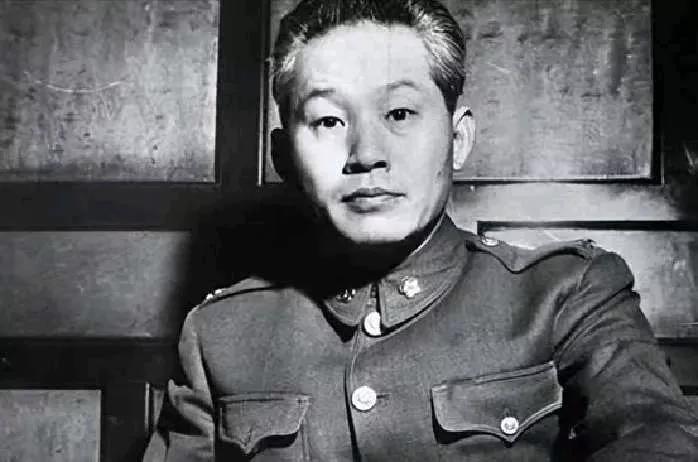1940年的一天,20岁的张爱玲正在房间里洗澡,母亲黄逸樊突然推门闯了进来。她来到张爱玲的身边,仔细地检查着张爱玲的身体。看到母亲这样做,张爱玲大怒道:“我是处女,你给我出去……” 这事儿得从张爱玲拿到第一笔巨额稿费说起。张爱玲像个得了宝贝的孩子,捧着一个厚厚的信封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信封里是一沓皱巴巴的港币,一块的、五块的,乱七八糟凑了八百块。这是她港大的历史老师佛朗士给她的稿费。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的笔,挣来的一大笔钱。 她当时有多激动呢?第一时间就想拿去给母亲看,就像我们小时候考了满分,第一个想分享的总是爸妈。她以为,母亲会为她骄傲,至少会觉得女儿长大了,有出息了。 可她把钱摊在桌上时,黄逸梵的脸瞬间就冻住了。她劈头盖脸地问钱是哪来的,听完解释后,眼神里全是怀疑和鄙夷,冷冰冰地说:“怎么能拿别人的钱?要还给他。” 张爱玲急得满头大汗,翻来覆去地解释这是稿费,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但黄逸梵就是不信。在她那个新潮又现实的世界观里,一个二十岁的女学生,靠写几个字就能挣到八百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她的思维立刻就拐到了一个最不堪的方向:女儿是不是和那个男老师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这钱,是不是“卖身”得来的? 这个念头一旦种下,就疯长成了参天大树。于是,就有了浴室里那场堪称惊悚的“验身”。 这件事发生后,张爱玲的心,算是彻底凉透了。她穿好衣服,一句话没说,把那八百块钱往客厅桌上一扔,摔门就走了。她当时可能还存着一丝幻想,觉得母亲就算不信她,好歹也会把这笔钱给她存起来,交学费也好,留学用也罢,总归是女儿的血汗钱。 可生活有时候比戏剧还讽刺。三天后,她去找母亲,正好碰上母亲的朋友来串门。一个阿姨拉着她闲聊,嘴快地说了句:“你妈妈昨天打牌手气真背,一晚上输了八百块,不多不少,就八百!” 八百块。 这个数字像一把锤子,狠狠砸在了张爱玲心上。她站在门外,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之前所有的委屈、羞辱,在这一刻,都化成了一种麻木的绝望。她后来在《小团圆》里写,感觉就像有件什么事结束了,不是她自己做的决定,但就是知道完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 自此之后,她对母亲,只剩下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冷漠。不是恨,也不是怨,就是那种“这个人从此与我无关”的疏离。 但你要说这对母女一开始就这么剑拔弩张吗?也不是。时间倒退两年,张爱玲还是个会拼了命奔向母亲怀抱的小女孩。 那年冬天,她刚从父亲张志沂的囚禁中逃出来。她那个抽大烟的爹,对她进行了一次堪称残暴的毒打,最后甚至抄起花瓶要往她头上砸。之后她被关在小屋里,生了重病,差点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死了。她抓住一个机会,像只惊恐的小兽,逃了出来,穿过上海冬夜的寒风,投奔了已经离婚的母亲黄逸梵。 那时候的母亲,在张爱玲眼里是女神。她时髦、漂亮、会说外语,浑身都散发着自由和新潮的气息。张爱玲崇拜她,依赖她,觉得只要能跟母亲在一起,做什么都愿意。 可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真正住在一起,问题全暴露了。黄逸梵是个有洁癖、生活极度西化的独立女性。她看不惯张爱玲生活上的笨拙和邋遢。而张爱玲,从小在旧式家庭长大,有保姆伺候,生活自理能力几乎为零。 黄逸梵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上流社会的淑女。她教张爱玲跳交际舞,教她走路要抬头挺胸,但张爱玲总是学不会,笨手笨脚。母亲让她自己削苹果,十八岁的张爱玲拿着刀,却不知如何下手。在黄逸梵看来,女儿简直是个废物,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 失望一天天累积,耐心一点点耗尽。母女间的温情,很快就被挑剔和争吵取代。黄逸梵的失望,最终变成了一句最伤人的话。有一次气急了,她对着张爱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两年的同居生活,已经让她们的感情充满了裂痕。而那八百块港币,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张爱玲来说,那八百块的意义太重了。它不只是钱,更是她在这个让她自卑的世界里,第一次找到的价值证明,是她的“生存证”。她终于可以挺起胸膛对母亲说:你看,我虽然不会跳舞,不会交际,但我能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 然而,母亲用最羞辱的方式,亲手碾碎了她的这份骄傲。 后来张爱玲远走美国,嫁给了赖雅。母亲在英国病危,写信求她见最后一面,她只是寄去了一百美金,冷漠得像个路人。直到母亲去世,留下了一箱价值不菲的古董遗物,指明要留给张爱玲。这些古董,在她后来最艰难的日子里,成了她的救命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