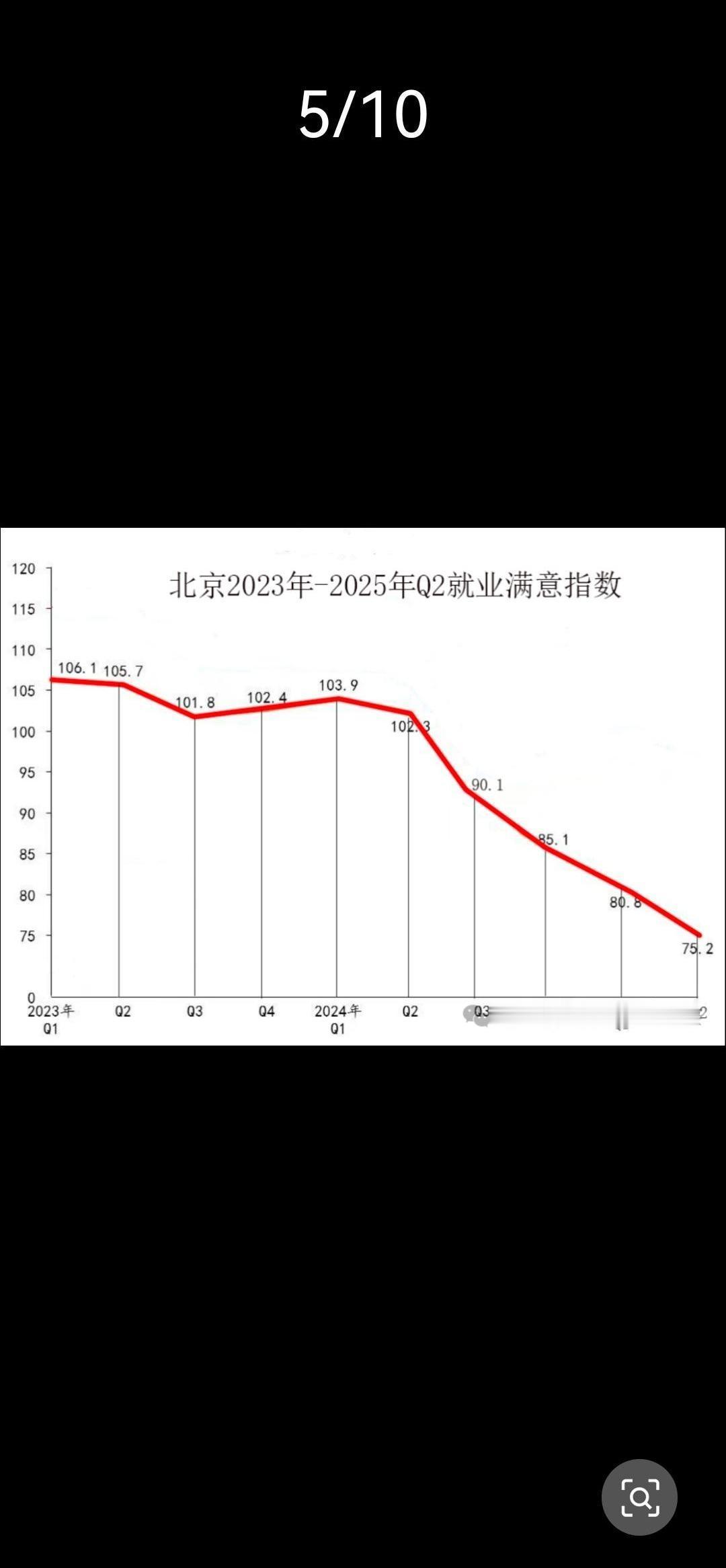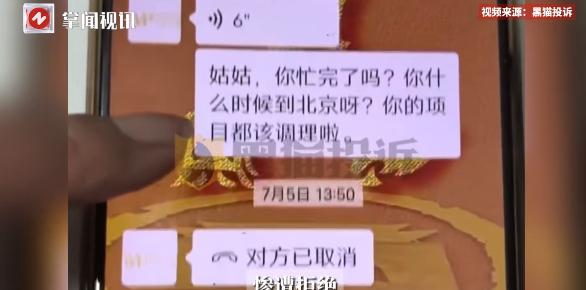1938年,一名外国婴儿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出生。可他的父母因为着急要回国,直接把他丢在了医院。 收养这个孩子的,是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中国办事处当高级职员的李先生和他的妻子赵秀珍。他们给孩子取名李忆祖,或许是希望他永远记住自己的血脉源头。 小忆祖的童年,在北京的胡同里度过。那头金色的卷发,让他成了孩子们中间最扎眼的存在。为了少些麻烦,他总是习惯戴着一顶帽子,试图藏起那张与众不同的脸。 好景不长,父亲英年早逝,抚养他的重担,全落在了母亲赵秀珍一个人的肩上。赵秀珍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山东女人,缠着一双小脚,却有着山一般的坚韧。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独自拉扯着孩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我母亲一辈子没享过福,但她总告诉我,人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要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这句话,李忆祖记了一辈子,也成了他一生的行为准则。 抗战胜利后,母子俩回到北京。李忆祖聪明好学,一路考上了北京二中。学校门口镌刻的校训——“为实现理想走进来,为服务社会走出去”,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扎了根。 高中时,学校组织了一次活动,让他们和“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专家吴运铎结成了对子。吴运铎在战斗中失去了四肢和一只眼睛,却依然为国家研制武器。他对学生们说:“我们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是生龙活虎的战士,随时准备到最艰苦、最困难、最需要的地方去……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 这番话,像一道光,照亮了李忆祖的人生方向。他当即跑到新华书店,买下吴运铎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他珍藏了一生,从北京带到了新疆,书页泛黄,边角破损,却承载着一个少年最初的誓言。 高考前夕,两个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来学校做报告,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在青海勘探的惊险故事——晚上睡帐篷,外面有熊出没。同学们听得心惊胆战,李忆祖却热血沸腾:“嘿!这太适合我了!” 高考志愿,他毫不犹豫地填下了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与找矿专业。 1962年,大学毕业的李忆祖面临分配。学校在北京,他本可以留在首都,过上安稳的生活。但他却两次打报告,主动申请去新疆。 当时,全国有志青年都响应着一个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李忆祖的专业,330名毕业生里,有70多人申请去新疆。 离家的前一晚,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粮食短缺。母亲赵秀珍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点猪肉,包了一顿饺子,默默地看着他吃完,然后把他送到火车站。新疆,在那个年代意味着遥远和艰苦,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她心里有万般不舍,但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让他留下来的话。 就这样,24岁的李忆祖,带着母亲“有骨气”的嘱托和偶像吴运铎的激励,坐上了西去的列车。 这一去,就是近六十年。 他在新疆煤田地质局156勘探队,一干就是22年。每年4月进山,9月才出来。天山南北,阿尔金山无人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和队友们四五个人一辆车,拉着汽油甚至炸药,在没有路的山里颠簸。车开不进去了,就背着几十斤的仪器徒步翻山越岭。 “我真没觉得特别辛苦,” 老人回忆起那段岁月,不以为苦,反而“嘿嘿”地笑了起来,“每天都很新鲜,找到了矿,就很高兴。” 野外工作充满了危险。一次坐车刚过桥,身后的桥就被洪水冲垮;在阿尔金山无人区,他从驴背上摔下来,又发着高烧,硬是忍着剧痛爬上了海拔4000米的检测点。 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也收获了爱情。他娶了同为地质工作者的苏州姑娘曹锦霞,把她接到了乌鲁木齐,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彻底扎下了根。 上世纪80年代,李忆祖从野外勘探一线转到了教育岗位,在单位的子弟学校当起了物理老师。1981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到1998年,他从乌鲁木齐市教育局退休。 本该颐养天年的他,却一天也闲不下来。他利用自己的地质知识和极强的动手能力,投身到了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中。他自己编写了近80万字的科普讲稿,自制了无数生动有趣的教具。 “我给孩子们讲磁悬浮,就弄两个磁铁,一个发电机,一通电,它就转起来了。让他们一看就明白,发明并不神秘!” 他的科普讲座,场场爆满,听众多达数十万人。为了讲课,年近古稀的他学会了用电脑,上网查资料。为了让孩子们更直观地了解新疆,2011年起,他担任央视《地理中国》摄制组的顾问,带着团队爬雪山、下冰川,一干就是8年。也正因为此,他的膝盖受到了严重损伤。 如今,80多岁的李忆祖老人,住在一间60平米的老房子里,屋里除了书,就是他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录像带、光盘和自制教具。有人称他“地质科学家”,他却连连摆手:“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地质工作者,退休后愿意给孩子们讲讲课。” 今年是他入党40周年,在给年轻党员的交流会上,他深情地说:“我是有外国血统的中国人,我是一位善良、淳朴的中国母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抚养长大的。所以不管到哪儿,我都有一颗永远不变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