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师长谭震林收到一份来自茅山的电报,忽然脸色大变,大声喊道:“你是不是译错了?再给我译一遍!”译电员委屈的重译,谭震林看完电报,呆呆的站着,半响说不出话。 电报是从茅山根据地发来的,内容简短得令人窒息:“十六旅罗、廖二同志于塘马战斗中壮烈殉国。” 罗、廖二同志,一个是十六旅旅长罗忠毅,一个是政委廖海涛。 这两个人,是谭震林一手带出来的兵,是他麾下最能打、最倚重的两员猛将,更是他风雨里并肩走过来的兄弟。 1938年,抗日的火烧遍了江南。新四军奉命东进,要在敌人的心脏地带——苏南,扎下一颗钉子。这地方,紧挨着南京、上海,是日伪统治的核心区。想在这儿站稳脚跟,比登天还难。带队的就是陈毅和谭震林。 谭震林,人称“谭老板”,打仗鬼点子多,性格又硬朗。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夸他:“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是谭震林。”他到了苏南,很快就相中了茅山这块宝地。山连着山,沟套着沟,正好跟鬼子玩捉迷藏。 罗忠毅和廖海涛,就是那时候跟着他打江山的左膀右臂。 罗忠毅是个湖北汉子,红军时期就是有名的战将,打起仗来不要命,人送外号“罗猛子”。他带着部队,硬是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把茅山根据地从无到有地拉扯起来。 廖海涛呢,是个政工干部,心思比针还细。部队里战士想家了,他能坐炕头聊半宿;根据地老百姓缺盐少粮,他能想办法从敌占区弄来。有“罗猛子”在前头冲锋陷阵,有廖海涛在后头稳定军心,再加上谭震林居中调度,这三个人硬是把茅山根据地经营得有声有色,成了插在敌人胸口的一把尖刀。 那时候的日子苦啊,战士们吃的是糙米,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军装。可人心是热的。谭震林常开玩笑说:“咱们这是‘叫花子’部队打‘阔佬’,得有股子穷人的狠劲儿!”罗忠毅听了就哈哈大笑,廖海涛则在一旁点头,盘算着下一批宣传标语该写点啥。他们三个人,就像一个稳固的铁三角,撑起了苏南抗日的一片天。 好日子没过多久,鬼子就急眼了。 1941年,日军调集了数万兵力,对我苏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清乡”和“铁壁合围”。坦克、大炮、飞机,能用的家伙全都用上了。他们的算盘打得很精:把根据地分割成小块,一块一块地“清剿”,让你跑都没地方跑。 局势一下子紧张到了极点。谭震林带着指挥部在溧阳的水西村,天天研究地图,头发都白了不少。他心里清楚,这时候最怕的就是硬碰硬,必须化整为零,跟鬼子兜圈子。 11月28日,一股日伪军突然扑向了十六旅的旅部所在地——塘马村。当时,罗忠毅和廖海涛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情况万分危急。 其实,他们是有机会突围的。警卫员几次三番地劝:“旅长、政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先撤吧!” 可罗忠毅把枪往桌上一拍,眼睛瞪得像铜铃:“撤?往哪撤?旅部一撤,部队就散了!老百姓怎么办?我罗忠毅的兵,没有当逃兵的!” 廖海涛也斩钉截截铁地说:“我们是部队的主心骨,主心骨不能倒!” 他们不是不知道留下来的危险。但他们更清楚,作为指挥官,在最危险的时候,你得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你的身影,就是战士们的胆气。 那天的战斗,打得天昏地暗。 日军的炮弹像犁地一样,把小小的塘马村翻了个底朝天。罗忠毅和廖海涛就在村口的祠堂里指挥,祠堂的墙壁被机枪打得千疮百孔。 警卫连的战士们,一个个都是好样的。子弹打光了,就端着刺刀冲出去肉搏。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立马补上。 罗忠毅亲自端着一挺轻机枪,对着冲上来的鬼子猛扫。他打红了眼,嘴里还不停地喊:“给老子狠狠地打!”廖海涛则在一旁,一边给伤员包扎,一边大声地鼓舞士气:“同志们,坚持住!党和人民看着我们!” 战斗从清晨持续到黄昏,警卫连的战士几乎全部牺牲。最后,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完了。日军黑压压地围了上来。 罗忠毅和廖海涛背靠着背,站在一起。罗忠毅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廖海涛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鬼子同归于尽。 那一年,罗忠毅37岁,廖海涛32岁。 两个正当年的汉子,把命留在了江南的这片红土地上。 译电员看着呆立在那里的谭震林,大气都不敢出。过了好半天,谭震林才缓缓地抬起头,眼眶红得吓人。他没有哭,也没有再发火,只是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说:“给他们……报功。告诉部队,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那声音很轻,却比任何呐喊都重。 巨大的悲痛没有击垮这位铁打的汉子。他擦干眼泪,立刻着手重新组建十六旅的领导班子,把部队的士气重新聚拢起来。他知道,对牺牲兄弟最好的告慰,就是把他们的旗帜继续扛下去。 很多年后,已经身居高位的谭震林,还时常会跟身边人提起罗忠毅和廖海涛。他说:“那两个家伙,都是好样的。我们说好了,要一起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结果他们俩,提前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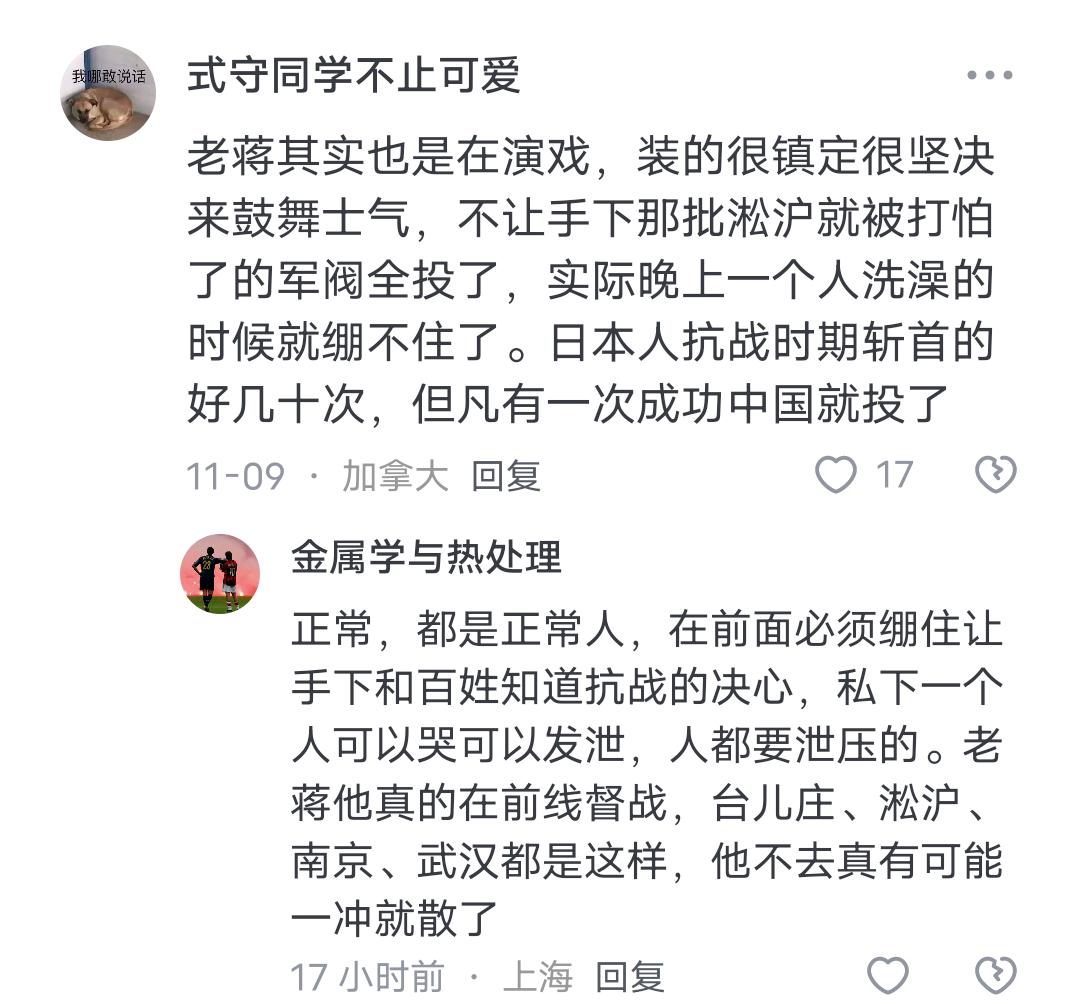







苏米
[赞][赞][赞]
用户10xxx39
谭老板有这个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