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越级提拔兵团部主任,授上将,2位兵团副司令很能打,授中将 “1951年初春,中央让您去三兵团接任政治部主任,马上动身吧?”简短一句,电话那头语气笃定。阎红彦放下听筒,只说了三个字:“遵命,走!” 对他来说,这一步来得有些突然。此前在晋冀鲁豫三纵,他只是副司令兼副政委,距离兵团领导层还有半级。可编制刚调整完,任命电报就飞到西安。有人打趣:“阎副司令直接跳格子,成了兵团首长,够快!”越级提拔在解放军不是没有先例,但落到这位陕北汉子身上,人们还是有点意外。 陕北红军出身的底色,是他手里最硬的一张牌。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在砖窑、土堡之间拉杆号召,硬是把分散的游击队拧成了一支能打正规仗的队伍。后来大部红军长征离陕,陕北依旧打着星星之火的旗号,这份功劳中央记得很清楚。 抗战爆发后,他调任警备旅政委,主业是稳住后方交通线。作战机会不多,却把地方、军队、游击组织全盘协同起来。有人说“这活儿不冒烟”,但没有后方,前线也立不住。抗战结束,他被派到晋冀鲁豫三纵,吃住都跟在部队一线。新乡、长葛、淮阳几仗打下来,才算把“地方干部”这顶帽子摘掉。 1949年,全军整编。陈锡联受命组建三兵团,麾下10军、11军、12军个顶个的老主力,可政治部主任人选迟迟没定。纵队政委们都在等,可电报最后钉在阎红彦名字上。陈锡联愣了愣,还是拍板:“行,他来。”这就是那次“越级”。 三兵团的阵容硬。副司令杜义德兼10军军长,王近山兼12军军长。俩人都是硬骨头:杜义德打南麻、临朐时顶过日军重炮;王近山更是夜袭阳明堡、千里奔袭运输线。行家里行都知道,这两位在牌面、军功和资历上,谁摆在正副司令位置都说得过去。 然而授衔名单里,阎红彦挂上将,杜义德、王近山却是中将。消息一放出,茶馆里议论不断:“这回四方面军吃亏喽!”事实没这么简单。1955年的授衔方案,除了战功、职务,还有一条暗线——各“山头”比例要协调。四方面军的上将名额早被叶剑英、陈赓等十来位占去,再加两人指标就超了。三兵团这桌牌,只能做减法。 有人问:“杜、王二位心里服气吗?”一位老通信员回忆,王近山哼了一声:“中将就中将,仗还咋打就咋打,别磨叽。”杜义德则更淡:“我打仗不是为了星星”。一句玩笑收场,实际却是真心话,他们更在意的是建军后部队能否继续摔打、练兵。 与此同时,阎红彦的岗位却悄然转弯。1956年,他南下云南,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实权不小,但云南边疆事务繁杂,军务只是挂名。他也清楚:“兵装脱得越久,越要学地方那一套”。之后几年,围绕土地、民族、边境贸易,他没少趟泥泞。1959年西藏局势紧张,中央点名要云南配合运输,他一句“尽量别让前线断线”—— 这话掷地有声,可见仍保留着军人那股子硬。 回头看,越级提拔并非凭空得来。第一,陕北根据地当年作用不算大,却撑住了红军北方火种,这份象征意义必须有人“代言”;第二,三兵团在大西南作战后,需要一个能统筹战场和地方的人,阎红彦兼而有之;第三,授衔时中央确实要给各块根据地留面子,红二、四方面军不能继续加码。权衡利弊下,这位老陕北最终挂上了上将肩章。 有意思的是,上将星挂到肩头,他在军中停留的时间却很短。授衔次年,云南农业社改、边境贸易、民族政策,全都压到他案头。时任云南军区参谋长的干部调侃:“阎政委依旧按军队作风开会,话一少,行事利索,不拖泥带水。”地方干部觉得新鲜,军队干部也服气。 1960年后,国内经济紧张,西南物资调拨紧绷,他仍然坚持每月到口岸转一趟,盯粮、盯盐、盯棉布,防止哄抬。有人私下里说:“阎书记手里那支皮鞭,军队和地方谁也不敢掉队。”半玩笑半敬畏,但也说明他的方式并未完全褪去军味。 遗憾的是,时代洪流来得太快。1966年风浪掀起,他被指责“打着上将旗号搞地方保护”,随后遭受冲击。1974年,一纸公报说他“因病医治无效”,年仅62岁。对于老三兵团的同志来说,这是心头难消的痛。陈锡联后来提起:“阎红彦这个人,脾气倔,但忠厚,事情交给他放心。”寥寥数语,足见评价。 杜义德与王近山的结局同样各有坎坷。前者转入南京军区后长期主持训练,帮助一大批基层指挥员成长;后者在风浪中被反复打击,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军功让他们立住身,人情世故却磨人心,这是很多将领共同的命运。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山头”平衡不存在,或许这三个人的星级会重新排序;但历史没有假设。半个世纪过去,尘埃落定,人们提起他们的名字,更多想到的是作战本领和干劲,而不是肩章颜色。军事史料里留下的数据,足够说明问题:三兵团鏖战西南,一年歼敌10余万,打开大后方,阎红彦统筹政治工作,杜义德、王近山指挥主力穿插进逼,这便是最直接、最朴素的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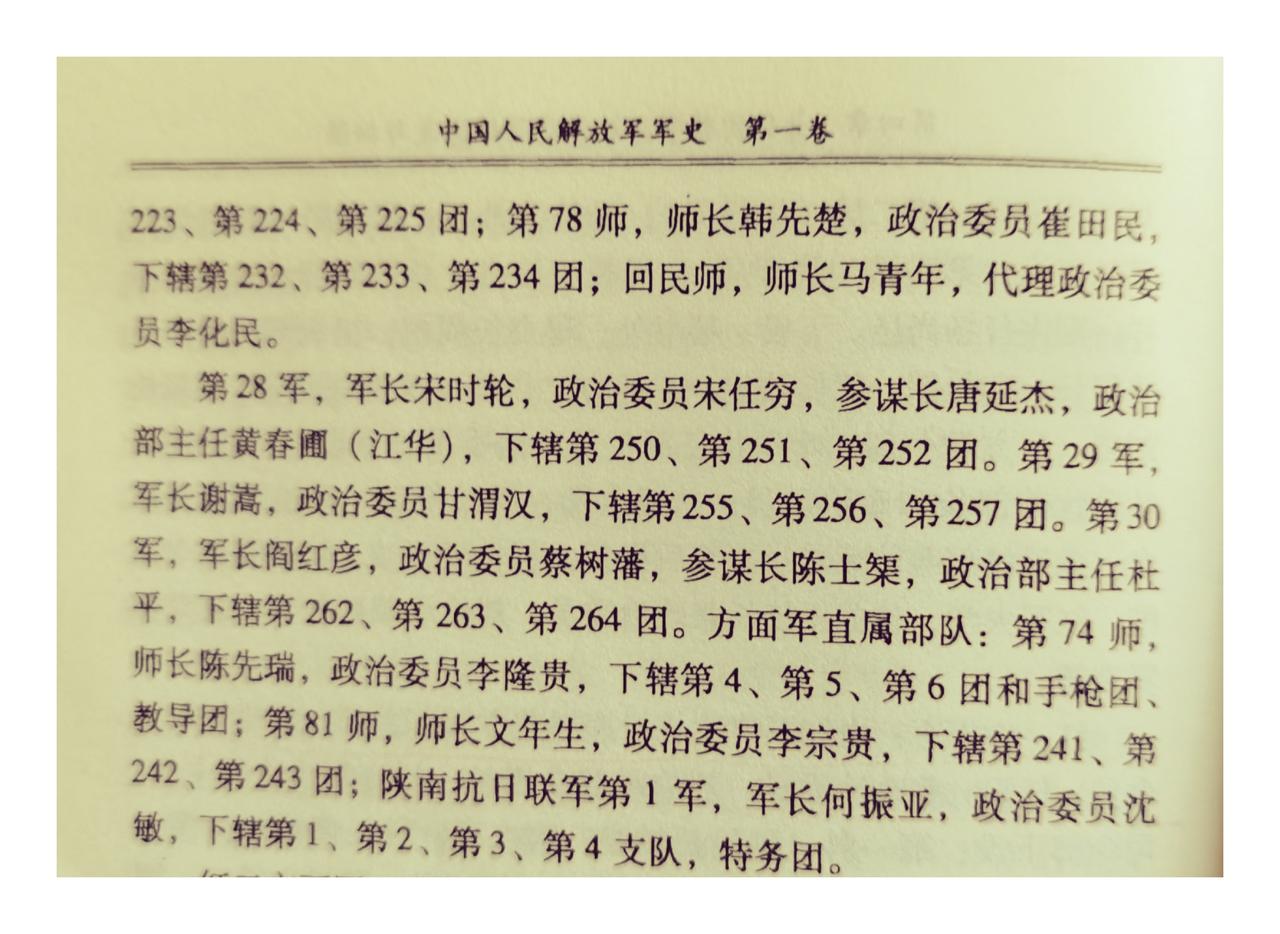






用户14xxx75
弥个大爷的,小片子胡拼乱写。
1100032
小编,你还是多去做梦为好! ”杜义德打南麻、临朐时顶过日军重炮;王近山更是夜袭阳明堡” ……说错误百出,那都是夸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