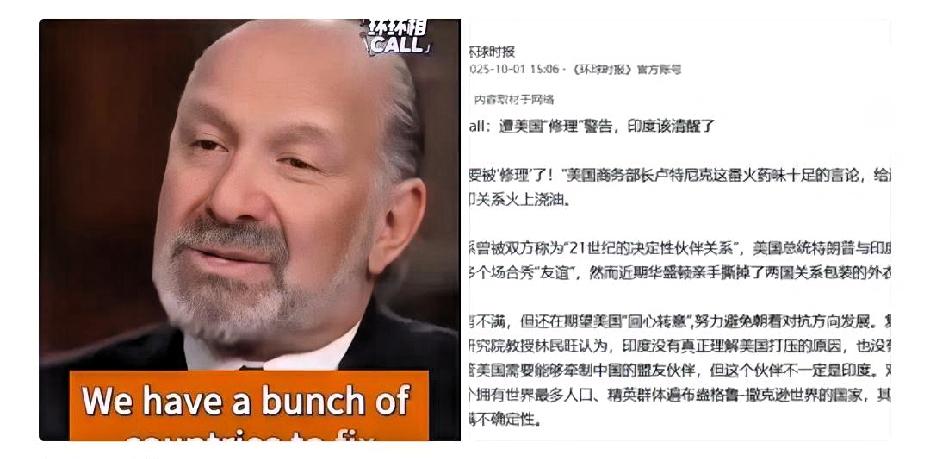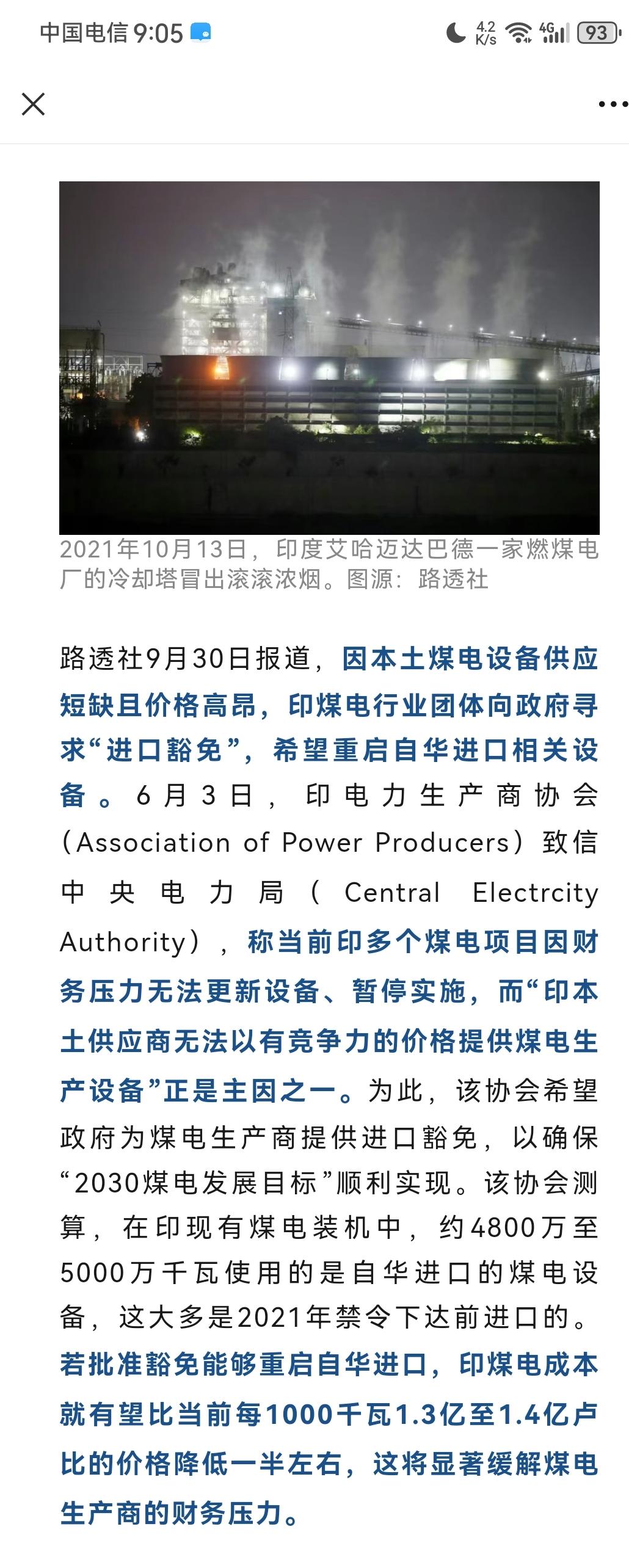【观点:印度裔美国人如何挽救美印关系】
(国会山报)当“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活动家劳拉·鲁默 (Laura Loomer) 在去年年底抨击“来自印度的第三世界侵略者”来到美国时,她的言论听起来像是边缘言论 。
但随着今年夏天美印关系出现二十五年来最严重的破裂 ,新一波反印度情绪席卷了新右翼——其根源在于对外包工作岗位的愤怒、对美国 收入最高的 少数族裔的偏见和嫉妒。
但最近针对印度和印度人民的转变也归因于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建设维持快速发展的美印伙伴关系所需的机构方面严重投资不足。
在美印关系更加紧密是应对各自面临的来自中国的重大“威胁”的最佳机会之际,印度裔美国人具有独特的优势来应对这一挑战。
从表面上看,认为美国民间社会尚未准备好支持美印关系的想法是违反直觉的。
印度裔美国人如今是 美国仅次于墨西哥的 第二大外国出生族裔,也是当今美国大学生的最大外国生源国 。即使你努力避免与印度人和印度裔美国人进行人际接触,也并非易事。
然而,这种交流的大部分只是单向的,很少有资源用于帮助两国相互了解。
即使不考虑大学生一直以来渴望的“背包游欧洲”留学项目,在印度留学的美国学生数量也少得可怜。在2022-2023学年,印度 接收的美国学生数量甚至落后 于加纳、南非和厄瓜多尔。
印地语是世界第三大语言,仅次于英语和汉语,但 领先 于西班牙语。
对现代语言协会 语言注册数据库的查询 显示,在有数据的最近一年中,只有区区 1,700 名美国大学生学习了印地语,与韩语、俄语和现代希伯来语等使用者人数很少的语言相比,这一数字相形见绌。
印度的精英阶层可能大多讲英语,但 独立调查“英语熟练度指数”发现,韩国、俄罗斯和以色列的英语普及率仍然超过印度。
东亚研究中心是美国大学的标配,而南亚研究中心却少见。尽管华盛顿的智库里挤满了欧洲、中东和亚洲的专家,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 即将成为第三大经济体的国家, 却被一小群孤僻的专家所笼罩。
制度上的差距是印度和美国臭名昭著的原因之一,两国让可避免的误解破坏了从技术、贸易到国防等各个领域急需的合作。
这种制度缺陷已不可持续——不仅因为 印度国内反印度仇恨情绪日益高涨 ,还因为没有任何双边关系对于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地缘政治挑战更为重要,因为中国对印度和美国都构成了严重威胁。
解决这个问题有行之有效的模式。尽管美国与日本和德国的亲密友谊在今天看来是命中注定的,但在二战交战双方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之后,这种友谊却并非显而易见。
通过美国慈善资助的组织(如美国德国理事会和大西洋桥)定期召集商界、政界和媒体精英, 对德国 产生了变革作用,日本协会和日本之家对日本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
尽管如今美国公众对以色列的支持正在迅速 下降,但几十年来,美国犹太人为加强美以关系所做的努力一直引人注目。
专注于犹太裔美国人的出版物构成了一个政治多元化的生态系统 ,完善了关于双边关系的思想网络。像 塔格利特的“以色列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样的项目 ,通过为犹太裔美国人提供全额资助的以色列之旅,让他们了解该国的文化和政治,增强了两国民间联系。
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和北京的苏世民奖学金都是为了在快速的地缘政治转型中,在大国之间建立精英桥梁而 设立的 。它们在构建跨文化的领导力网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印度早就应该采取自己急需的与这些举措相当的举措了。
所有美国人都有责任建设推动美印伙伴关系向前发展的公民社会,而印度裔美国人则拥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引领这一进程。除了跨文化技能外,印度裔美国人卓越的经济成就也为他们提供了推动这些举措所需的资源。
最重要的是,他们卓越的业绩表明,只要印度裔美国人接受挑战,他们就能拥有改变美印关系所需的毅力、智慧和职业道德。
——作者比尔·德雷克塞尔是哈德逊研究所战略与美国治国方略中心的研究员,专注于技术竞争和美印关系。尼拉贾·德什潘德是一位作家兼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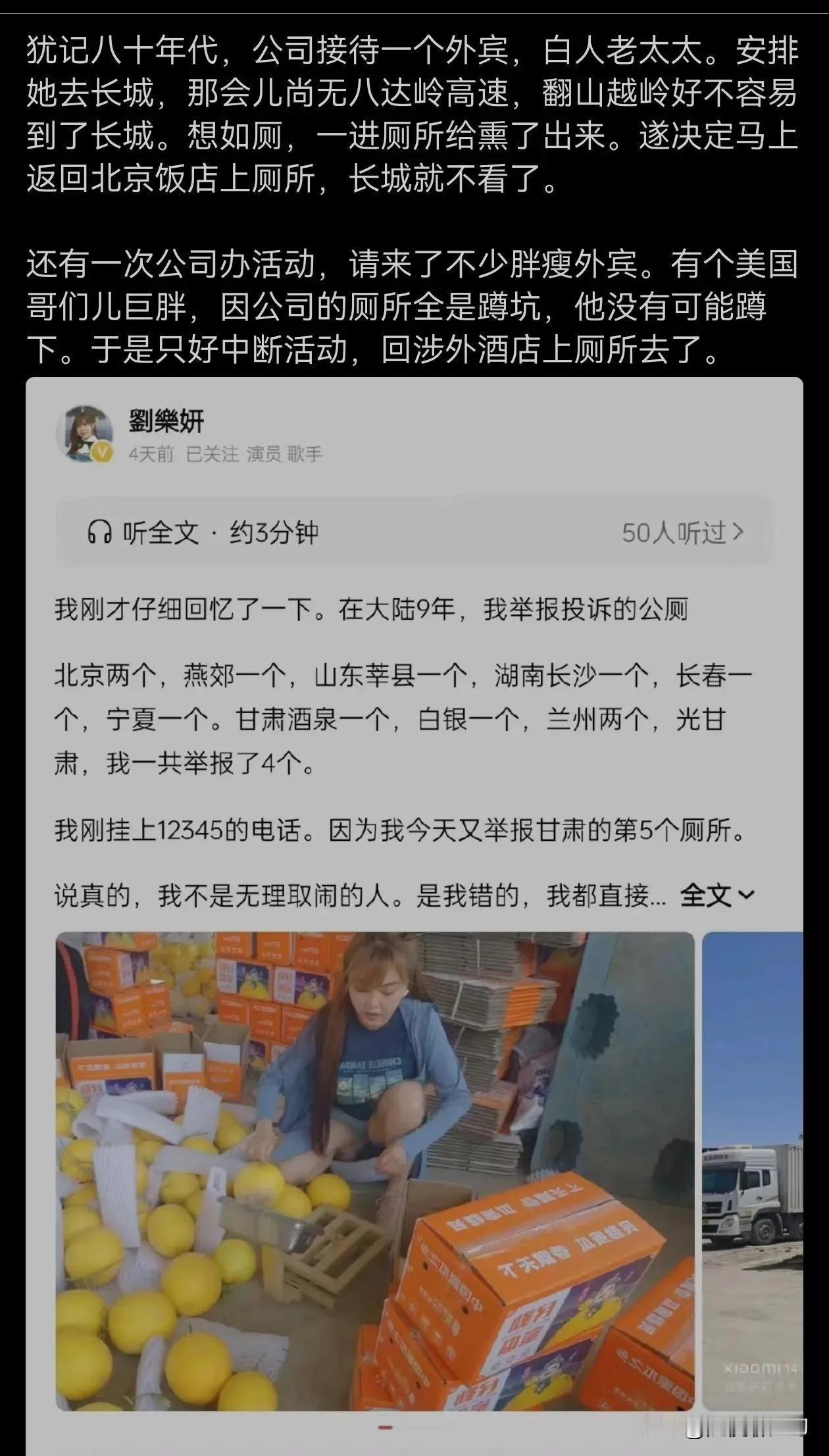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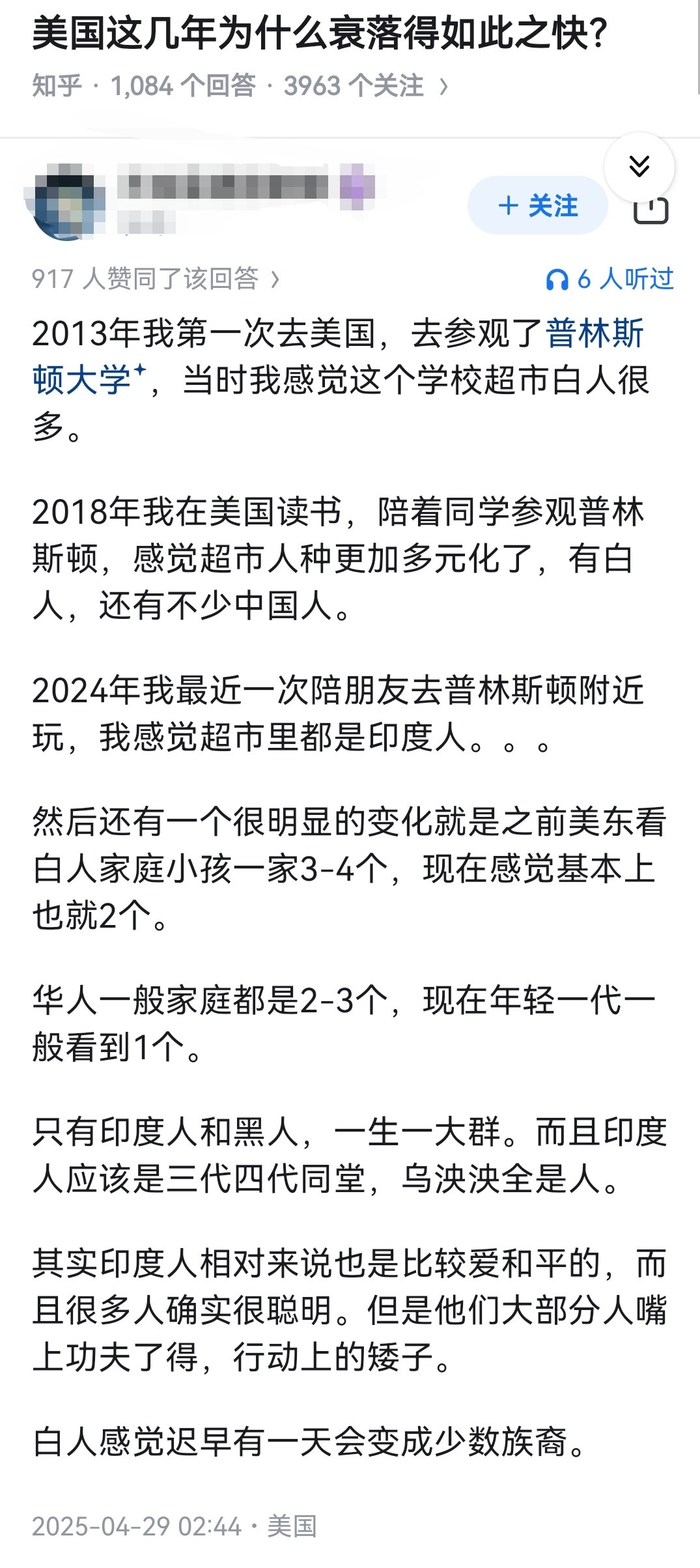

![印度要能做到这些就不是印度了[吃瓜]](http://image.uczzd.cn/12821051507046433960.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