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提到继母朱枫时,85岁的阿菊声音依旧冷硬:“我不想再提她。”一句话,让人心头一紧。 85岁的阿菊端坐在藤椅上,声线冰冷,不带丝毫温度,淡淡道:“我不想再提她。”她手里攥着一块洗到褪色的蓝布帕子,一遍遍地擦着自己的膝盖。那条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 旁边的人好心提醒,继母朱枫当年对她多好。阿菊像是没听见,只是更用力地擦着膝盖。这股冷硬的背后,不是恨,而是一种被时光磨得粗糙的疼。 这疼痛的源头,也曾有过最温暖的模样。比如那个绣着歪扭小红花的花布书包,那是继母朱枫亲手缝的。阿菊命运不济,亲娘早早离世。木匠父亲秉持重男轻女的陈旧观念,在他看来,让女娃读书纯属浪费之举。 是朱枫,那个穿着月白旗袍的继母,为了她读书的事跟丈夫叉腰吵架,吼出那句“女娃读书才知道外头的天地大”。后来,朱枫掏出自己的嫁妆钱,把阿菊送进了学堂。 每天早上,阿菊的书包里都揣着一个热乎乎的煮鸡蛋。晚上,朱枫就陪着她写作业,自己在灯下做针线。阿菊发高烧那次,也是朱枫背着她去诊所,路上摔了一跤,自己膝盖磕破了血直流,却死死护着怀里的孩子。 彼时,阿菊会轻启朱唇,一声“娘”,如春日微风中绽放的花朵般甜美,轻柔地唤出,似能融化世间的一切坚冰。这份情感如此真实,以至于多年后,当阿菊在台湾生下孩子,手忙脚乱之际,她写的家信第一个想到的求助对象,就是这位远方的母亲。 可谁能想到,这封充满女儿依赖的家书,落在某些人眼里,竟成了一张进入台湾的“完美通行证”。那份被悉心珍存的亲情,宛如一层密不透风的屏障,成了最为缜密的伪装,将内心的真实悄然隐匿,让人难窥其背后的真相。朱枫临行之际,寄给丈夫一张照片,背后题着“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这看似寻常话语,实则是一场悄无声息却饱含深情的诀别,令人动容。 到了台湾,母女俩短暂团聚。阿菊很高兴,常买继母爱吃的凤梨酥。她只觉得朱枫有些怪,总在晚上关着门写东西,说是家书。她不知道,那些普通的饼干盒里藏着微缩胶卷,而每周六“去药店”的借口,是为了与吴石中将秘密接头。 日常的物件,性质悄然改变。一张普普通通的台币,被朱枫随手记下了阿菊家的电话,本是为以防万一。可当1950年初,地下党领导蔡孝乾叛变,这张为了应急的台币,瞬间变成了一张精准的地图,把致命的危险直接引到了阿菊家门口。 极具讽刺意味的,恰是那张本为逃生准备的军机通行证。它仿佛是荒诞现实的一个注脚,无声却又强烈地揭示着某些令人唏嘘的真相。那是吴石冒险安排的生路,办理时甚至还得到了阿菊丈夫王朴的协助。然而,这张“希望”的存根在吴石办公室被搜出,反而成了锁定朱枫位置的催命符。 希望破灭了。接下来就是枪托撞门的巨响,一群制服人员冲进家中。朱枫被带走时回头看了一眼,那眼神复杂到阿菊一辈子都忘不掉。她吓得腿软,只能紧紧抱着怀里的孩子。 一夜之间,整个家都被毁了。丈夫被调离岗位,薪水减半;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骂她家“窝藏坏人”;孩子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为了活下去,为了保护家人,阿菊学会了一句话:“她是共匪,和我们没关系。” 当朱枫牺牲的消息传来,阿菊躲起来,哭了一整夜。从此,恐惧成了扎进心里的刺,那个“娘”字,她再也不敢提起。 很多年后,这段历史有了不同的结局。朱枫的遗骸成了一个传奇。由于工作人员将她的本名“朱谌之”的草书错认成“朱湛文”,那个小小的骨灰罐竟奇迹般地在台北富德公墓躺了60年。 2010年,这个编号77的罐子被外孙女护送回大陆,安葬在烈士陵园,朱枫作为英雄的故事终于完整。她的名字被刻上丰碑,供人敬仰。 可阿菊呢?她的信物是另一件东西。在悉心整理旧物之际,她的指尖不经意间再度触碰到那个色泽已然褪去的花布书包。往昔时光似在这一触间悄然涌动。摩挲着上面歪扭的小红花,老人眼眶泛红。朱枫的骨灰罐是留给国家的宏大记忆,而这个书包,是只属于她一个人的、被恐惧囚禁了终身的微弱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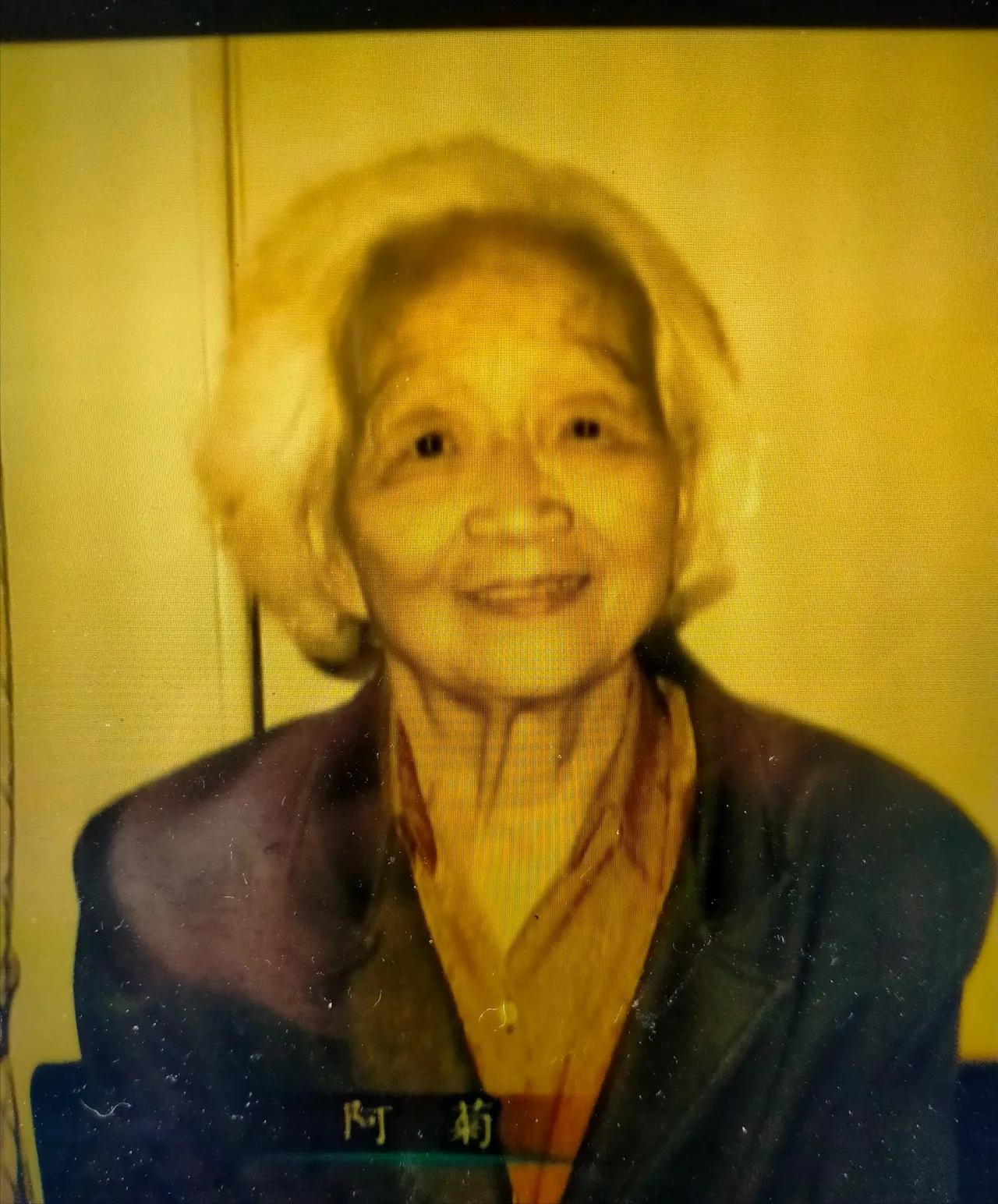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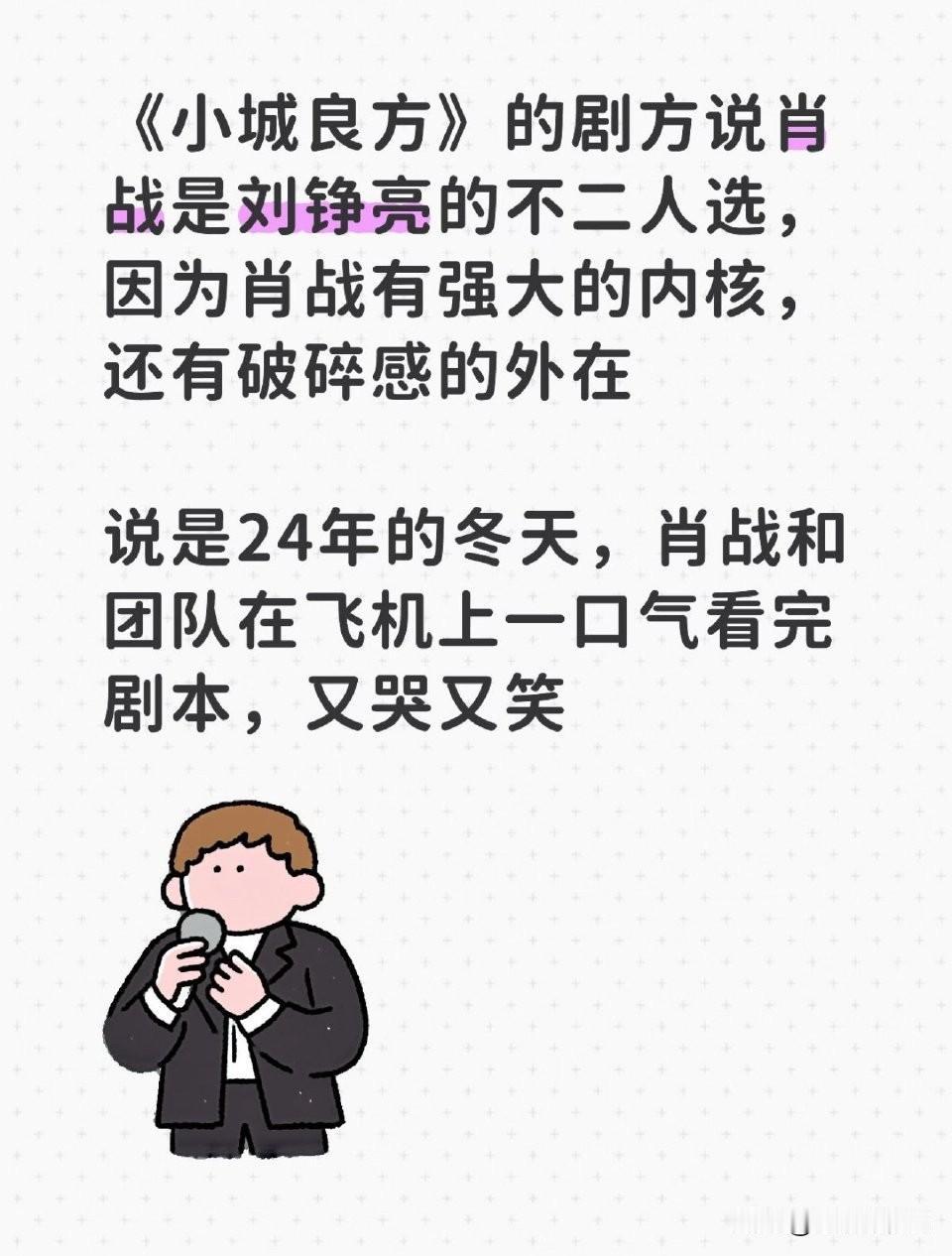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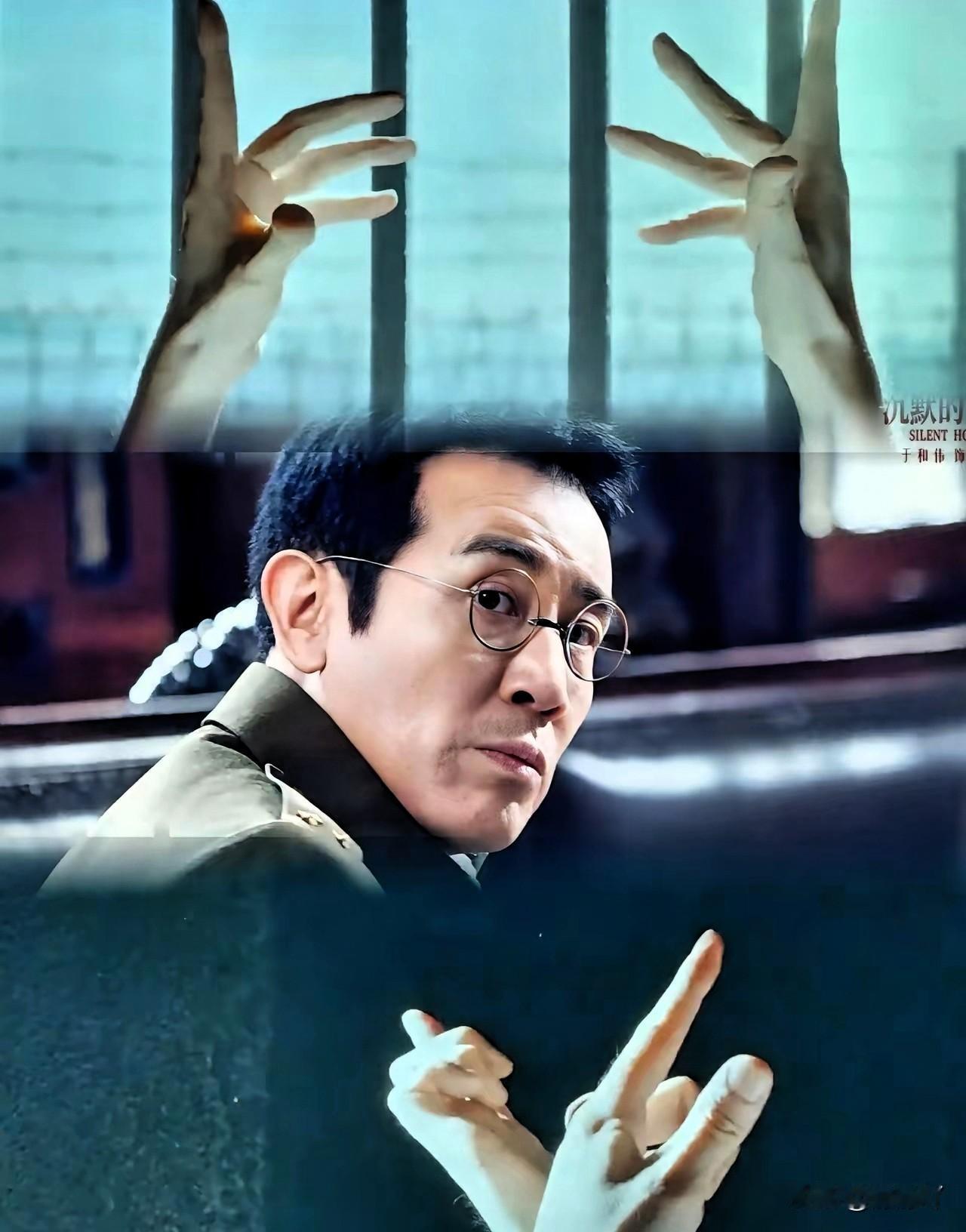

胡汉三
阿菊有一个亲姐在北京,打过一次电话给阿菊,后来就打不通了。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