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个乌军士兵,举着白旗走出来,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求饶。是:“不是我们不想守,是没人管我们了。” 废墟里走出来的人,一个个神情呆滞,白旗举在手上,没人喊投降,也没人哭,几乎所有人都盯着前方,像是还在等什么指令。 双方走到十米远时,举白旗的瘦高个先开了口,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每个字都裹着累。他没求饶,也没辩解,对着俄军士兵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是我们不想守,是没人管我们了。” 这话里的无力,是一天天熬出来的。这个小阵地原本守着一个加强排,算上后来补的新兵,满编时有五十多人。他们刚到这儿时,上级说会按时送补给、派增援,可从来没兑现过。 头一周还能靠无人机投点压缩饼干和水,从第二周起就断了粮,无线电里只剩滋滋的电流声,不管他们怎么呼叫指挥部,那边都没半点回应。 瘦高个叫瓦列里,战前在基辅开汽车修理厂,口袋里揣着张皱巴巴的全家福,照片边缘都磨卷了,上面的妻子和女儿笑得很真。瓦列里跟俄军士兵说,他们最后一次收到指挥部命令是十天前,就五个字:“死守,不许退”,之后再没任何消息。 阵地左侧火力点被俄军炸掉时,他们紧急呼叫炮火支援,无线电里只飘来一句模糊的“再扛扛”,接着就彻底没声了。阵地上的水第五天就没了,士兵们只能接雨水、刮树叶上的露水喝。 三个新兵喝了变质的积水发高烧,没药,只能用湿泥巴敷额头降温。其中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没熬过去,咽气前还攥着妈写的信,纸上的字早被泪水泡花了。瓦列里和战友把他埋在阵地后面的弹坑里,没墓碑,就捡了块平整的弹片插在土堆上,用刺刀刻了名字和入伍的月份。 这样的绝境,在如今的乌军前线不算新鲜事。巴赫穆特打了好几个月,早就成了俄乌双方的绞肉场,乌军好几支最精锐的部队都在这儿打光了。 俄军事专家弗拉季斯拉夫·舒里金之前公开说过,乌军在这场战斗里死了大概五万人,受伤和失踪的加起来有十二万,一百多辆坦克、两百门火炮还有一千多辆装甲车都被打坏了。 这些数字背后,全是像瓦列里这样的士兵——不是不愿打,是连最基本的吃喝弹药都凑不齐。 压垮士兵们最后一点斗志的是第七天发生的事。阵地上的无人机侦察设备没电了,彻底成了瞎子,连周围的情况都摸不清。有人用望远镜看见远处有车队过来,以为是增援,激动地挥信号旗,等车队近了才看清是俄军的补给车。双方交了火,乌军没多少子弹,只能躲着打,当场就没了两个战友。 更让士兵们寒心的是,前线和后方完全是两回事。瓦列里的战友安德烈被弹片划中左腿,他们用卫星电话叫医疗救援,那边说“救援不够,得排队”。 这队排了三天,安德烈的伤口烂得发臭,最后是战友用烧红的刺刀消毒,硬生生把弹片挑了出来。后来安德烈才知道,他们守的地方被指挥部划成了“次要阵地”,补给和救援都先给了那些“关键阵地”,而那些所谓的关键阵地,不少都是指挥层在地图上画出来的。 乌克兰作家安东·尼尔曼在文章里写过类似的事,他说前线士兵和后方人之间,早隔了一道看不见的墙。 基辅的公园里,常能看见缺胳膊少腿的老兵坐在长椅上抽烟,这些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成了后方人想躲开的存在。尼尔曼的母亲宁愿绕路,也不愿从公园穿过,她说看见那些老兵心里发慌。 这种别扭,正好说透了前线和后方的状态——后方人在停电和防空警报里过着平常日子,前线人却在废墟里赌命。 瓦列里和战友决定投降那天早上,把最后三发子弹留了下来,不是要自杀,是怕走出废墟时被流弹打到。他们用刺刀在铁皮上刻了“我们投降,别开枪”,和白旗一起举着。 走出废墟前,所有人都对着阵地鞠了一躬,那下面埋着战友,也埋着他们一开始的那点士气。 俄军士兵按战俘待遇给他们拿了吃的喝的,热汤端过来时,好几个人的手都在抖——他们已经四天没吃过热东西了。瓦列里喝着汤,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因为投降丢人,是想起了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 他想,要是指挥部能早送点补给,要是救援能快一步,那孩子说不定还能活着见到妈。 红军城的战场上,也有一样的事。那边的乌军被俄军围住后,指挥部照样下命令“死守”,却没说怎么增援、怎么撤退。乌军总司令亲自派了十一个特种兵空降,想在包围圈里建个落脚点,结果刚落地就被俄军全部消灭。 这种明摆着送命的行动,没挽回战局,反倒让下面的士兵彻底明白,自己就是指挥层博弈时可以扔的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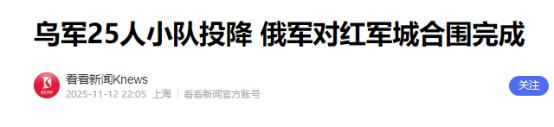






打坏公司
乌贼死不足惜
降魔金刚
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