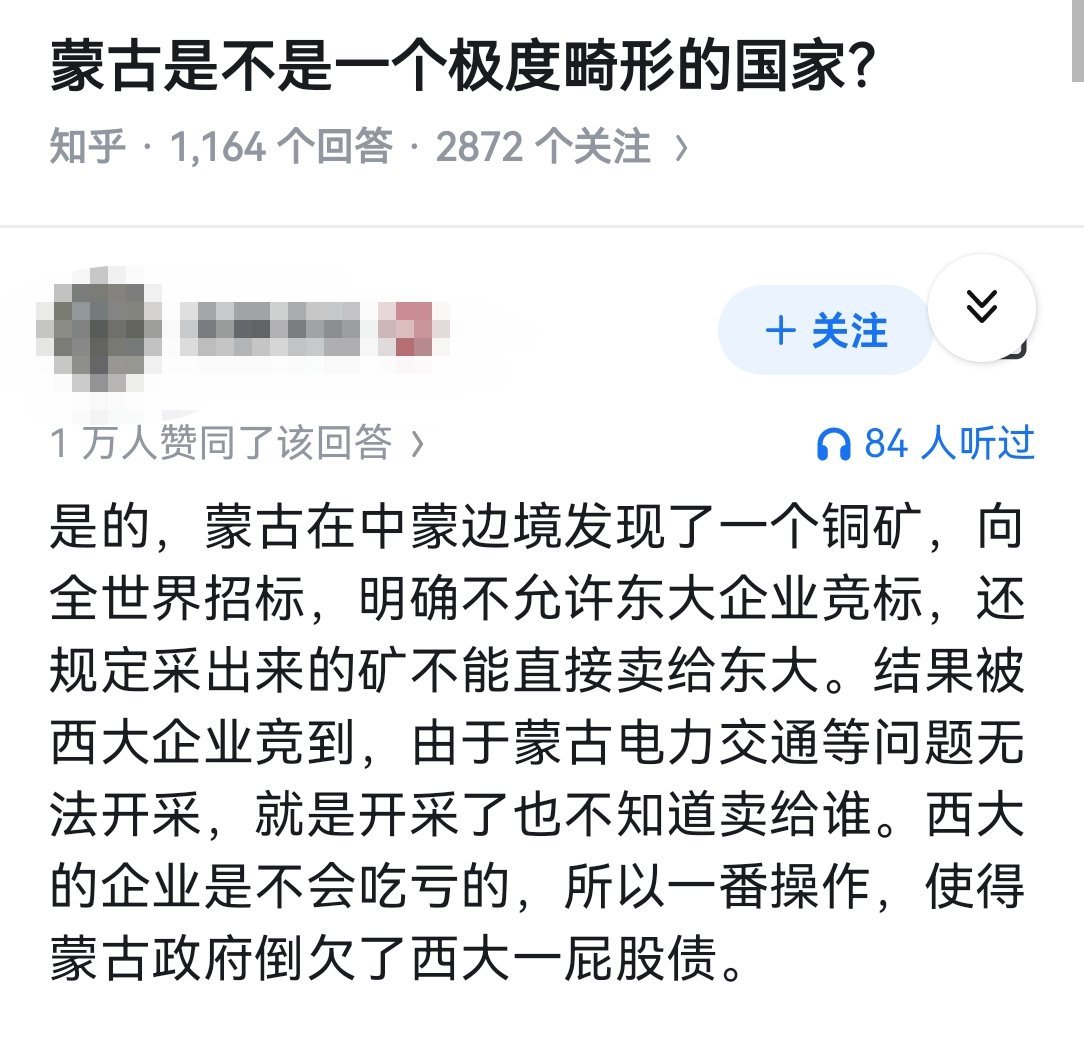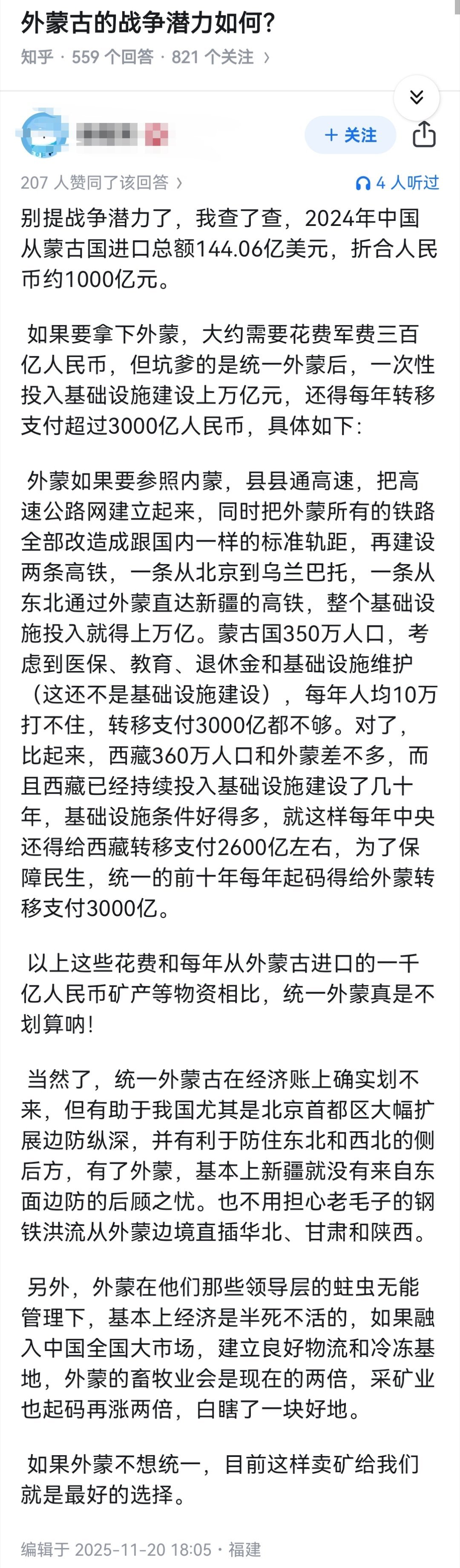1926年的蒙古大街上,到处都是梅毒晚期的人,鼻子都烂没了。1926年,有一苏联医生于库伦(现称乌兰巴托)的街上漫步,返回后暗自在笔记中记载,每十个牧民之中有一个脸部塌陷如同被斧头削平的山丘,他所言并非麻风病,乃是梅毒三期最为厉害的模样,也就是鼻软骨被侵蚀后留下的空洞,当地人称很多人为“马阿日格”,即“无鼻者” 1926年的库伦,当时如果有外来的旅人走在这座城市里,即便把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半张脸,眼前的景象也足以成为那一代人的噩梦:街上来来往往的成年人里,每隔十个,就有一个人的面部是塌陷的。 苏联考察队初到此地时,也被这种极高比例的畸形吓懵了,医生们甚至一度以为撞上了大规模的麻风病暴发,然而,当真正凑近去观察那些溃烂的边缘,嗅到那种特殊的腐肉气味时,才发现这是进入第三期的晚期梅毒。 这些被称为“马阿日格”的牧民,其鼻中隔软骨已经被梅毒螺旋体彻底啃食殆尽,面部的塌陷只是冰山一角,在那时的档案记录里,一场没有硝烟的瘟疫正在将这片草原推向种族存续的边缘。 这一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那时的旅蒙商队在运来茶叶和布匹的同时,也把脏病带进了草原,到了1912年局势动荡,外蒙闹独立,虽然多了不少俄国顾问,可正经的医疗卫生力量几乎是空白。 在缺乏管控的流动人口和混乱政局下,原本可以通过简单手段控制的病菌,在封闭的环境里如入无人之境,档案显示,当年的皮毛生意火爆,许多牧民拿值钱的皮子换烧酒,在酒精和欲望的催化下,蒙古包成了病毒最初的温床。 而那时候王公贵族盛行的一夫多妻制,又让这病毒迅速完成了从上层到底层的全方位渗透。 草原人好客,见面递鼻烟壶是规矩,也是交情,但这只小小的壶在十几个人手中流转,鼻烟壶的嘴就在十几个人的鼻腔黏膜上蹭过,病毒根本不需要那层私密的窗户纸,光靠这“友谊的传递”就足够完成指数级的扩散。 而在信仰最虔诚的寺庙里,致命的循环同样在上演:喇嘛给信徒行“圣水礼”,几百人排队共用一个不清洗的银碗。 前面人的唾液还没干,后面的人就虔诚地凑上去喝,人们本是为了祈求健康和平安,却不曾想那盛满圣水的银碗边缘,爬满了致命的梅毒螺旋体。 在青霉素尚未普及的年代,绝望的牧民只能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荒诞的偏方上,这反而成了比瘟疫收割人命更快的镰刀。 当时的喇嘛庙流传着一种“猛药”:把水银混合着刚杀的狼血,涂抹在溃烂的伤口上,甚至制成药丸吞服。 这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以毒攻毒”,在鄂温克旗曾有一位传奇的老猎人,年轻时能百步穿杨,后来因为染病,梅毒侵蚀了他的骨头,他拉弓时肩膀关节发出嘎吱嘎吱的骨头摩擦声,疼得连驯鹿都追不上。 为了治好这怪病,他也成了这些土法子的受害者,那些含有剧毒水银的“圣药”并没有长出新的鼻子,反而制造了更加痛苦的死亡。 许多病人还没等到病毒完全摧毁身体,就先死于急性汞中毒:牙齿松动脱落,头发成把地掉,全身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肾脏迅速衰竭。 苏联医学队后来的统计触目惊心: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因病死亡的蒙古牧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被水银和狼血“治死”的,那高达30%的死亡率背后,是一场愚昧与绝望并存的悲剧。 即便侥幸活下来,这种痛苦也会顺着血脉流向下一代,在1926年的牧区,很难看到活蹦乱跳的孩子。 梅毒的母婴传播导致大量孕妇流产或产下死胎,而那些命大活下来的婴儿,有三分之一患有先天性梅毒性角膜炎——他们的眼珠像蒙着一层浑浊的厚奶皮,生来便看不清这绿色的草原。 这不仅是肉体的溃烂,更是一个民族体质的全面崩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苏联医疗队带着强制性的卫生隔离政策进驻,并最终等到青霉素被像黄金一样运进草原,那满大街“无鼻人”的恐怖景象才逐渐从现实退回到泛黄的历史照片里。 参考资料: 《呼伦贝尔盟卫生志》 《蒙古地区性病防治史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