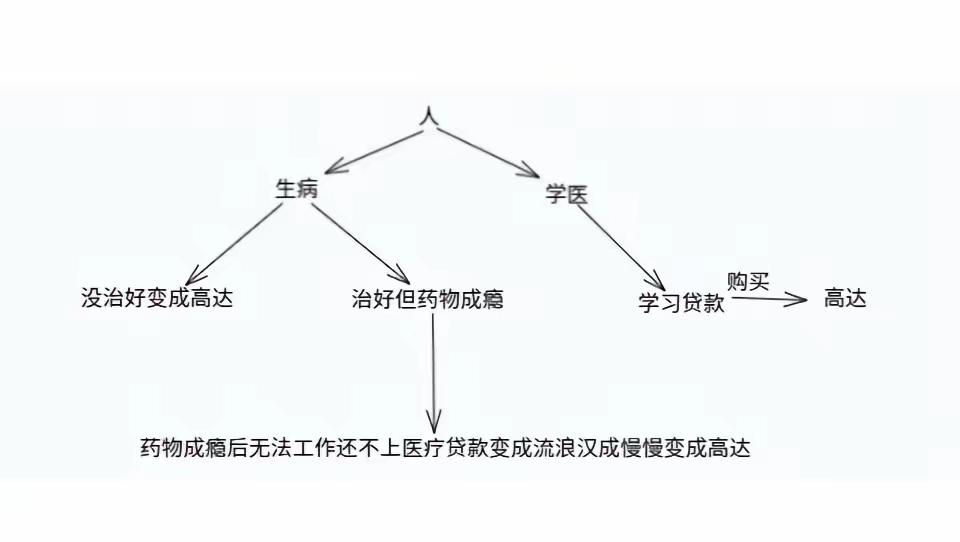美国长期迷信计算机模拟空气动力,高超音速飞行器研发进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当年钱学森认为,6马赫,8马赫,15,35马赫的空气动力特性会变化,于是坚决推动风洞建设。于是中国人一手风洞,一手计算机模拟。而美国一门心思搞计算机模拟,实际上6马赫的速度下,计算机模拟很好,但是更高速度,有了更多变量。 这种路径选择的偏差,早在冷战后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冷战时期美国其实在高超音速技术研究上起步不晚,1954 年就启动了高超音速发动机计划,还研制出 X-15 试验机,1967 年创造了 6.72 马赫的飞行纪录,积累了早期技术基础。 但冷战结束后,美国觉得实体风洞建设成本高、试验周期长,不如把资金和精力集中在计算机模拟上,认为凭借超级计算机和 CFD(计算流体力学)软件就能精准破解所有气动难题,这种认知让他们逐渐放弃了对先进风洞的持续投入,走上了单一依赖模拟仿真的研发道路。 他们没意识到的是,计算机模拟在低马赫数场景下的准确性,到了高马赫数领域会彻底失效。 6 马赫以下时,气流运动相对规律,软件还能做出较为精准的预判,但一旦速度突破这个阈值,飞行器周围会出现激波叠加、空气分子解离、原子电离等一系列复杂的热化学反应,甚至会形成等离子体鞘层,这些极端环境下的变量根本无法被现有软件模型完全覆盖。 更关键的是,美国 NASA 主导研发的 Vulcan-CFD 这款核心模拟软件,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无法精确预测飞行器表面的化学成分变化和温度分布,这直接导致研发出的部件在真实飞行中无法承受高温环境,连光电信号采集和通信都无法正常实现。 这种技术层面的先天不足,让美国多个高超音速项目接连折戟。 2010 年和 2011 年,美国空军的 HTV-2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两次试飞,都因为气动不稳定和热防护失效导致飞行器烧穿解体,最终这个项目只能彻底终止。 2021 年,美军寄予厚望的 AGM-183A(ARRW 项目)首次挂载试射,甚至出现了助推器未能成功点火的低级失误,导弹只能随载机返回基地,后续多次试射也未能彻底解决问题。 陆军的 LRHW 项目同样波折不断,多次出现助推器分离失败、滑翔体姿态失控等故障,始终无法稳定获取有效试验数据。 反观中国的研发路径,从一开始就确立了 “风洞 + 计算机模拟” 的双轨并行策略,而这一正确方向的奠定,离不开钱学森的远见卓识。 作为最早定义 “高超声速飞行” 概念的科学家,钱学森早年在美国就深耕风洞研究,深知不同马赫数下气流特性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他明确提出 6 马赫以上的高超音速领域,必须依靠真实的吹风试验来验证,不能单纯依赖理论计算。 回国后,他坚决推动中国的风洞建设,让中国从一开始就避开了单一依赖计算机模拟的陷阱。 从 2008 年 JF-12 风洞立项,到 2012 年完成验收,中国用四年时间建成了首座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复现风洞,之后又持续攻关,2018 年启动 JF-22 超高速风洞研制,2022 年完成首次运行实验,2023 年通过结题验收。 如今这两座风洞形成了完整的试验体系,JF-12 能模拟 25 到 60 公里高空、5 到 10 马赫的飞行条件,JF-22 则能覆盖 40 到 90 公里高空、10 到 30 马赫的极端环境,成为全球唯一能覆盖全部高超音速 “飞行走廊” 的实验平台。 更值得一提的是,JF-22 的喷口直径达到 2.5 米,比国外同类风洞大 1 米,像东风 - 17 这样的乘波体弹头无需做等比例缩小模型,直接用实物就能进行试验,获取的数据更贴近真实飞行状态, 这让中国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研发迭代速度大幅提升,能够提前发现并解决气动设计、热防护等核心问题。 美国直到中国 2019 年东风 - 17 高超音速导弹公开亮相后,才真正意识到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差距,紧急加速 ARRW、LRHW 等项目的推进,但此时他们的试验设施短板已经无法弥补。 美国现有的老旧风洞大多只能满足低速或低马赫数的试验需求,直到近年才开始推进 10 马赫级风洞的建设,而这种水平的风洞技术,相当于中国 20 年前的发展阶段。 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各军种在高超音速项目上各自为战,陆军、空军、海军分别推进不同的研发计划,需求差异大且缺乏协调,导致部分项目重复建设,资源严重浪费。 到 2025 年,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依然没有任何一款能够实现实战部署,而中国凭借双轨并行的研发策略,已经在该领域形成稳定优势。 中国始终坚持理论计算与实体试验相结合,通过持续建设先进风洞筑牢研发基础,才得以在激烈的技术竞争中占据主动,这种发展模式也印证了钱学森当年的判断,只有尊重科学规律,兼顾理论与实践,才能在前沿科技领域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