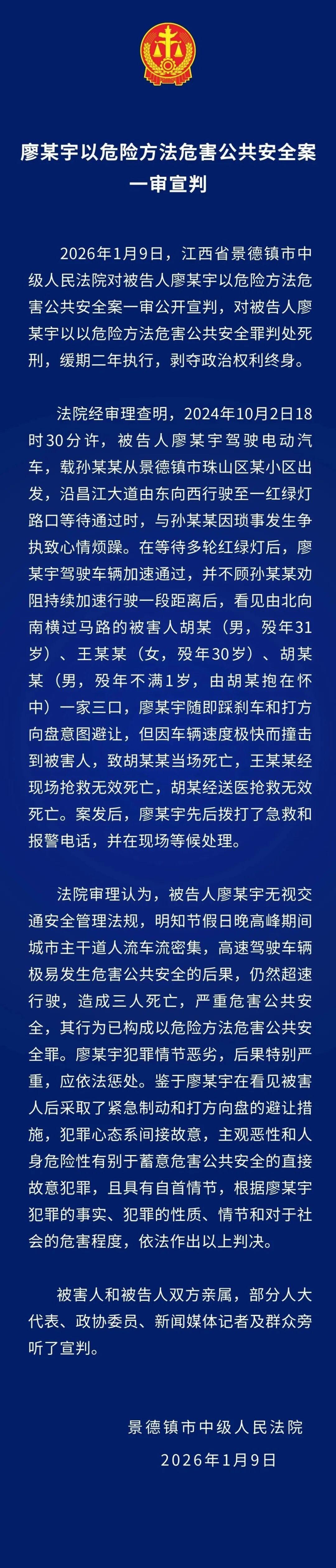廖某宇案与孙伟铭案本质不同。孙伟铭因酒驾导致四人死亡,初审被判死刑,上诉后改为无期,因为他非主观故意并积极赔偿,且邻里证言良好。而廖某宇案恶劣,他与车内人员争吵后故意加速至130公里,主观放任事故发生,甚至可视为故意杀人。一审判死缓显然过轻。 先回望 2008 年震惊全国的孙伟铭案。彼时的孙伟铭,还是个在成都打拼的普通上班族,没考驾照却敢长期无证开车,案发当天中午为亲属祝寿,喝得酩酊大醉后仍执意驾车。 酒精模糊了他的判断力,车子在成龙路失控,先追尾一辆比亚迪,紧接着越过双实线,接连撞上四辆正常行驶的轿车。这场惨烈的碰撞,让四个家庭瞬间崩塌,两对夫妇当场殒命,还有一人重伤。 一审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他死刑,彼时舆论一片叫好,觉得 “马路杀手就该重罚”。但上诉后,判决改判为无期徒刑,这份改判并非法外开恩,而是基于对主观心态的精准界定。 案发后他醉酒昏迷,清醒后得知后果吓得浑身哆嗦,第一时间委托父亲变卖财产赔偿。更关键的是,他的家人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拼尽全力筹款 11.4 万元赔偿被害人,后续又通过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取得了被害方的部分谅解。邻里和同事的证言也显示,他平时并非暴戾之人,只是案发时的侥幸与放纵酿成大错。 法院最终认定,他的主观恶性远低于直接故意驾车撞人的犯罪,再加上醉酒后对自身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改判无期符合 “罪刑相适应” 的原则。 再看廖某宇案,同样是高速飙车酿惨剧,性质却恶劣得多。2024年10月2日,景德镇的昌江大道正值节假日晚高峰,人流车流密集,这条限速 40 公里 / 小时的城市主干道,本应是最需要谨慎驾驶的地方。 可廖某宇因为和同车的孙某某发生琐事争执,心情烦躁之下,竟在等待多轮红绿灯后猛地加速。车子像脱缰的野马,速度一路飙升到 128.96 公里 / 小时,是限速的三倍多。 要知道,他在景德镇生活多年,清楚这条路的路况;他还曾向朋友炫耀过肇事车辆的加速性能,对车子的危险性心知肚明。 当他看到正在过马路的胡某一家三口时,才慌忙踩刹车、打方向盘,但极高的车速让避让毫无意义。一声巨响后,未满周岁的婴儿当场死亡,年轻的父母也相继离世,一个完整的家庭瞬间被碾碎。 案发后廖某宇虽报了警、在现场等候,构成自首,也有过避让动作,但这些都无法抹去他加速时的主观恶意。他不是醉酒失控,而是清醒地选择用 “高速飙车” 宣泄情绪,明知在人流密集的主干道超速会大概率引发伤亡,却毫不在意、听之任之 —— 这种 “放任”,比孙伟铭的 “醉酒失控型放任” 恶性得多。 法律上的间接故意,也分 “被动失控” 和 “主动制造风险”。孙伟铭是醉酒后对风险失去控制,而廖某宇是主动把自己和他人置于极端危险中,用公共道路当情绪的宣泄场。前者的风险是 “意外失控的衍生品”,后者的风险是 “刻意追求的发泄工具”,这正是两案最核心的本质区别。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判决结果的对比。孙伟铭造成四死一伤,二审因积极赔偿、主观恶性相对较轻改判无期;而廖某宇造成一家三口灭门,手段更恶劣、主观更放任,却只判了死缓。 或许法院考量了廖某宇的自首和避让情节,但这些情节能否抵消三条人命的重量?被害人家属在等待判决的两百多天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和应激障碍,天天闭门不出、整宿失眠,他们唯一的诉求就是死刑立即执行,为逝去的亲人讨回公道今日头条。当 “死缓” 的判决落地,这份痛苦无疑又被加重了一层。 司法裁判的意义,不仅是惩罚罪犯,更是警示社会。孙伟铭案的改判,传递的是 “知错能改、积极弥补可获宽宥” 的导向;而廖某宇案的轻判,却可能让公众产生 “情绪失控飙车杀人,最多判死缓” 的误解。 在车水马龙的公共道路上,每一次刻意的危险驾驶,都可能让无数家庭陷入灭顶之灾。法律对这种 “以公共安全为代价宣泄情绪” 的行为,必须保持足够的威慑力。廖某宇的行为,已经突破了公众对 “过失犯罪” 的认知底线,接近了 “故意杀人” 的恶性程度。 公共道路不是私人的情绪宣泄场,每一位驾驶者的方向盘里,都握着他人的生命。廖某宇案的一审判决引发争议,恰恰说明公众对 “严惩马路杀手” 的期待从未改变。 希望司法机关能正视这份争议,在二审中重新审视案件的恶性程度,用公正的判决守护公共安全的底线,告慰逝去的生命,也给社会一个明确的警示:任何漠视他人生命的行为,都必将付出最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