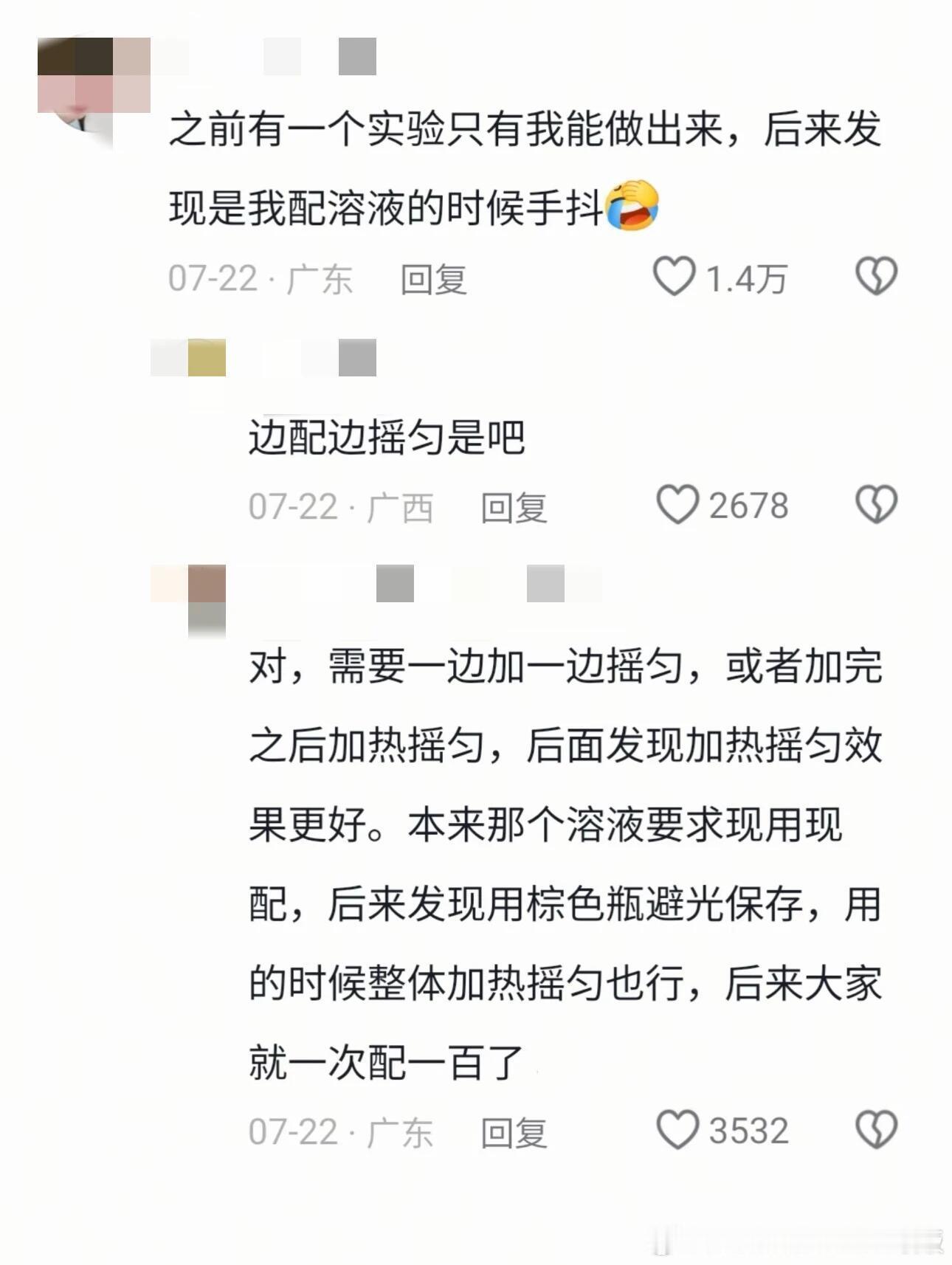征方腊后,燕青找到卢俊义,低声道:“主人,我想宰了吴用,报仇雪恨!就是吴用,害得咱们家破人亡!”卢俊义长叹一口气:“吴用,也是宋江指使的,你敢宰了宋江?马上就封官进爵了,算了吧!”燕青气得捶胸顿足:“主人,梁山没有好下场,跟我一起走吧!” 夜色像块浸透墨汁的破布,沉沉地压在杭州城外的残营上头。营火有气无力地跳着,映得卢俊义半边脸晦暗不明。燕青就蹲在他跟前,眼睛里那簇火苗子比地上的柴堆烧得还旺,压着的嗓音里带着铁锈味儿:“主人,那狗头军师,我今夜就能摸进他帐里!” 卢俊义没立刻接话,目光越过燕青的头顶,望进一片虚无处。风里裹着江南潮湿的泥腥和一丝难以消散的血气。方腊是剿了,可梁山带来的兄弟,十亭里折了七亭。林冲瘫了,秦明没了,武松断了一条膀子,昔日热烘烘的聚义厅,如今想起来竟像上辈子的事。他喉咙里滚出一声叹息,沉甸甸地砸在两人之间的空地上:“小乙啊,你那把伶仃刀,宰得了一个吴用,宰得尽这‘忠义’二字么?” 燕青霍地站起身,筋骨噼啪轻响,像张绷紧的弓:“忠义?他们拿这俩字当绳子,套了咱们多少年!害得您好好一个河北大员外,家产抄没,成了草寇;害得我……我燕小乙这条命,从东京城的锦缎堆里,滚到这血泥塘里!源头不就在他吴用那儿?几句歪诗,一场腌臜算计,把您逼得无路可走!这仇,就罢了?” 卢俊义抬手,止住他岩浆般喷涌的话头。那手曾使得动麒麟黄金枪,挑遍河北无敌手,如今指节粗大,覆着层洗不净的茧子与旧伤疤。“你只看见吴用。可那计策,没宋公明点头,他使得动?眼下是什么光景?尸山血海蹚过来,为的什么?不就是博个封妻荫子,青史留个‘忠良’名?宋江哥哥日日与那宿太尉、张干办周旋,笑脸赔尽,为谁辛苦?眼看就要论功行赏,衣锦还乡……这时候动他心腹,咱们前头流的血,算白流了么?” “衣锦还乡?”燕青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声音猛地拔高,又硬生生掐断,成了从齿缝里挤出的气音,“回哪门子乡?大名府的卢家庄早叫官府铲平了!咱们是贼,主人!在朝廷眼里,永远是梁山泊的贼!今日能用咱们打方腊,明日就能用别人打咱们!宋江哥哥……他那是鬼迷心窍,做着忠臣良将的梦呢!您瞧瞧这满营伤号,听听夜里那些憋着的呻吟,这就是咱梁山的‘好下场’!” 他胸膛剧烈起伏,猛地蹲回卢俊义脚边,扯住主人那陈旧战袍的下摆,声音里透出罕见的哀求与绝望:“主人,我燕青这辈子没求过您什么事。咱走吧!天下之大,江湖之远,寻个僻静处,我打猎砍柴,奉养您终老。强过在这腌臗局里,等着被人当棋子,用完就扔!” 卢俊义的眼神终于动了动,落在燕青年轻却饱经风霜的脸上。这孩子,是他从街上捡回来的孤儿,名为主仆,实如父子。燕青的机灵,燕青的忠勇,燕青那身东京城淬炼出的见识,比他这主人看得清啊。心里那潭死水被投入巨石,剧烈晃荡起来。走?说得轻巧。走了,就是背弃“兄弟”,就是坐实“反贼”,一生骂名。不走?眼前仿佛已看到高耸的宫门,冰冷的御阶,还有那帮文官们皮笑肉不笑的嘴脸。吴用?不过一条善于揣度主人心思的聪明狗。宋江?又何尝不是被“招安”二字迷了心窍的可怜人? 他想起擒方腊那一战,惨烈得如同修罗场。梁山的气数、魂灵,仿佛都折在那片江南水泽里了。剩下的,不过是些顶着旧日名号的空壳,等着朝廷施舍一点残羹冷炙。燕青的话,句句如刀,扎在他那层用“忠义”和“功名”糊起的铠甲上,露出里面早已冰凉的血肉。 营外传来巡夜梆子声,空洞地响了三下。更远了,隐约有将领营帐中的丝竹笑闹飘来,那是提前开始的庆功宴。这边是伤残与死寂,那边是醉生与梦死。一道无形的裂痕,早已将这支残军劈开。 卢俊义闭上眼,良久,重重叹了口气,这口气仿佛把他脊梁里最后一点支撑也抽走了。他没看燕青灼灼的目光,只望着地上摇曳将熄的火影,喃喃道:“走?……又能走到哪儿去呢。咱们的命,从上了梁山那天,或许就由不得自己了。” 燕青眼里的光,一点点黯下去,像燃尽的炭。他知道,主人这关,终究是没过。那份根深蒂固的“体面”与“名分”,还有对宋江残存的、近乎愚执的“义”,锁住了他。燕青慢慢松开攥着衣袍的手,退后两步,整了整自己那身同样破烂的衣衫,忽然抱拳,深深一揖。再抬头时,脸上已没了激动,只剩一片令人心悸的平静。 “主人保重。燕青……去了。” 他没说去哪,转身就走,瘦削的身影眨眼就融进帐外浓得化不开的黑暗里,悄无声息,仿佛从未出现过。卢俊义伸出手,想喊住他,喉咙却像被什么堵死,发不出半点声音。只有那冰凉的夜风,灌进他大张的嘴里,直凉到心底最深处。 他独自僵在火堆旁,直到那点火光彻底熄灭,四面八方的黑暗涌上来,将他吞没。远处隐约的笙歌还在飘荡,像一场华丽却虚妄的葬礼序曲。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