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四平,邓华和吴富善都不在纵队,指挥权交给他,战后调任司令 “1948年1月5日夜,命令下达了吗?”贺晋年把电台耳机放下,一句低沉的询问在指挥所里回荡。参谋回答:“邓司令还在哈尔滨疗养,吴政委北上开会,司令部只剩您决定。”对话不过十余字,却清晰标志出当时七纵的微妙处境——两位正职同时不在,战役号角却已吹响。 时间退回到1947年秋末。东北战场经过夏、秋两季攻势,国军主力被连番消耗,然而省城据点仍固守顽强,尤其是四平街这块“硬骨头”。七纵刚补入三千多新兵,邓华判断部队需要在较弱之敌身上积累攻坚经验,于是把锦州至义州一线几支地方保安旅列为首要目标。贺晋年此时初到纵队,先在合江军区、骑兵纵队积累的剿匪经验派上了用场——他熟悉处理零散抵抗与流动战的节奏。法库之战,七纵以兵不满万歼敌一千七百,虽是中等规模,却让新兵迅速完成“新老交接”。这一仗后,纵队气势回来了,总部嘉奖电报也随之而至。 进入冬季攻势,东北野战军主力陆续向铁岭、彰武、四平一线推进。邓华因肺气肿、气管炎被命令休养,吴富善又奉调参加“东北军政干部会议”。客观上,七纵成了一支“缺口”部队。能否自我运转,关系到整个正面战局。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胡奇才养病时,韩先楚多次代表四纵出战,已经给林彪、罗荣桓留下“副职也能挑担子”的印象。如今,贺晋年面临类似的考验。 他接手后的第一场硬仗是大孤家子围歼战。敌新三十七师一个团凭借丘陵地形抵抗顽强。贺晋年改变七纵以往单纯平推的打法,指令两团迂回切尾,主力夜袭其炮兵阵地,用八二迫击炮在两小时内击穿敌支撑点。天亮时,团部广播向残敌喊话:“你们已被包围,弹药还剩多少?”对方沉默,随后举旗投降。当日报捷电文写:“俘敌一千六百四十余,缴重机枪三十挺。”数据之外,更重要的是验证了“副司令—参谋长”组合的自主作战能力。 1948年初,二纵、七纵受命向新民方向佯动,以掩护主力南压四平。因邓华、吴富善均未返队,此次行动决策完全落在贺晋年肩头。他在作战会议上只说了两句:“方向必须飘忽,声势必须扎实。”于是,以旅为单位的夜袭、白天小分队袭扰、铁路封锁同步展开,国军新五军疲于奔命,判断“共军主攻新民”,被迫固守西侧。林彪看了战报,只批示一句:“声东击西,可行。” 到了三月,战役重心终于集中到四平。前三次攻打四平,七纵两进两退,对城防工事摸得清楚却没能一举拿下。此番再战,东北野战军集结了三千门火炮、三个主力纵队,志在必得。贺晋年给七纵下的新指令极为简单:“所有营以班排为单位建立‘穿插组’,炮火停止一分钟后即向城内纵深推进,不返回,不等待。”当晚二十一时,总突击发起,七纵在东南角撕开缺口,二纵于西北角合围,火力交织之下守军被割裂成数块。3月14日拂晓,四平内外枪声渐稀,守敌一万八千人悉数被歼。 战后统计,七纵在攻城阶段歼敌五千余,伤亡却控制在一千三百以内,这样的战损比让林彪、罗荣桓十分满意。罗总政委在点评中写道:“贺晋年同志组织周密,敢担责任,值得表扬。”随即,东北野战军组建新序列的五纵、十一纵、十二纵,冀察热辽军区的地方武装整编为十一纵,司令员人选,军委直接点名——贺晋年。 不少干部私下议论:“七纵还没打完收官战,这么快就调走合适吗?”电报回复给出的理由仅一句:“四战四平,知其难度者方能独当一面。”换言之,连续攻坚磨砺出的指挥员,正是扩大战略进攻所必需的:既理解城市攻坚,又懂得运动歼敌。 而十一纵先天条件并不好。部队多是由冀东地方队伍扩编,武器轻,训练粗。贺晋年上任伊始,先把赖以成名的夜袭、包围、切尾等战术拆分成课目,照着东北主力的标准重新训练。辽沈战役打锦州外围的义县时,十一纵完成阻敌增援的重任;平津战役期间,部队在新保安一线执行分割包围;解放海南岛计划未能成行,十一纵又被南调,两年里几乎没有真正休整。 回看他在七纵的那段“代班”经历,很难说是偶然:正职缺位、战役紧迫、部队新老交替,恰好把需要统筹、果敢、细致的要求叠加在一起。也正是这份历练,让一位陕北红军出身、曾长期以“剿匪专家”面目的将领,在东北烈火中完成了向野战军主攻司令的转型。 遗憾的是,十一纵在1950年整编为陆军三十八军后,贺晋年调往军委,与昔日部下又分道而行。有人问他是否怀念四平街。贺晋年淡淡一句,“那是一座被炮火翻过四遍的城,留给它的情感,只能是完成任务。”军事指挥员的冷峻,由此可见一斑。 四战四平,表面看是一座城市的反复易手,深层里却是对军队组织力和指挥链的严酷检验。邓华养病、吴富善开会,七纵并未陷入指挥真空,恰恰相反,副职临危受命展现了灵活与担当。这样的制度与人才储备,成为后来东北战场连战连捷的一枚关键拼图,也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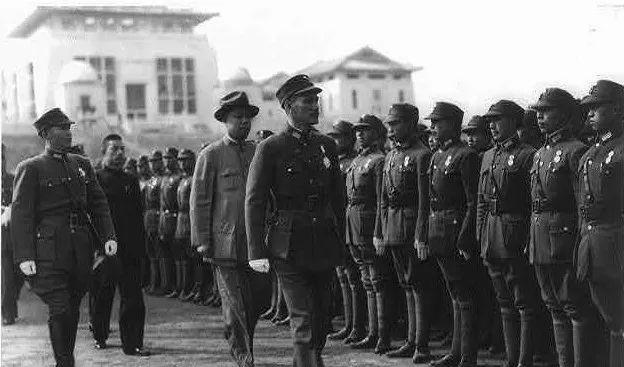


用户10xxx68
十一纵何时改编三十八军?小编改的
用户15xxx92
胡吊扯!十一纵称38军,那一纵能愿意。一纵能吃了十一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