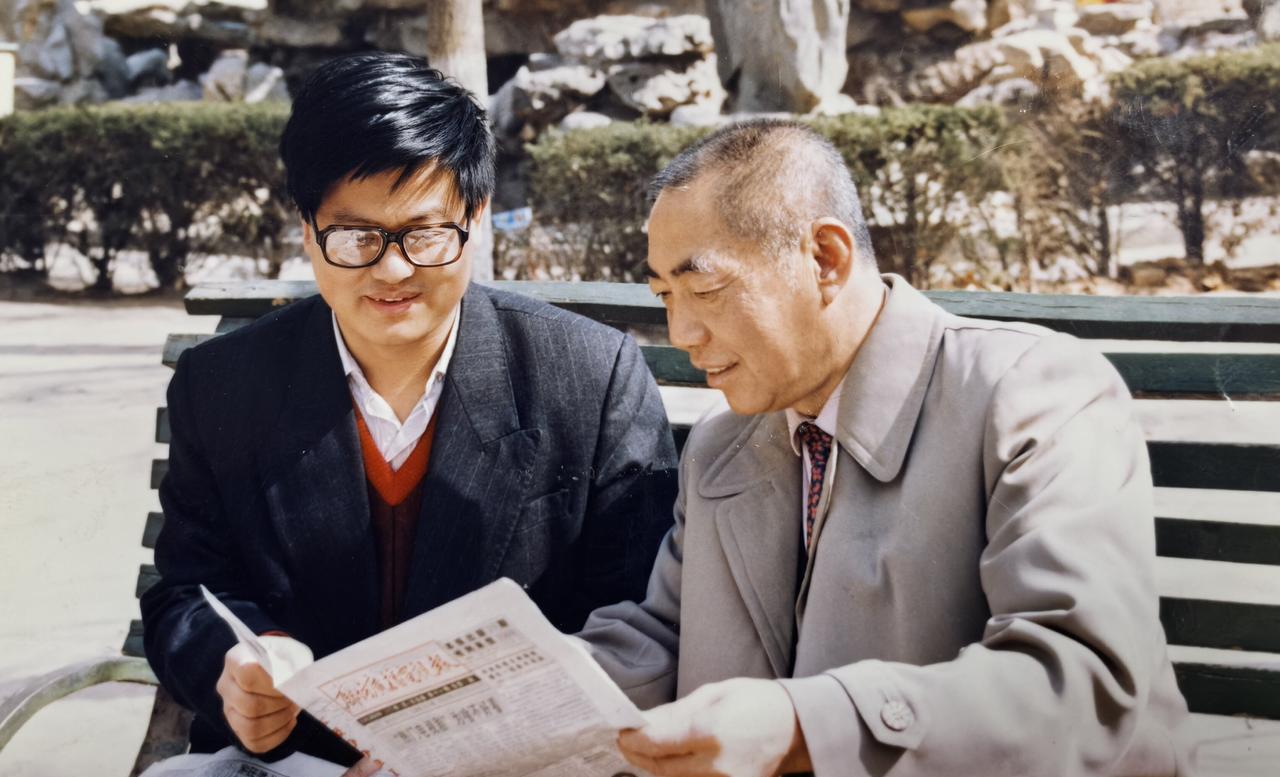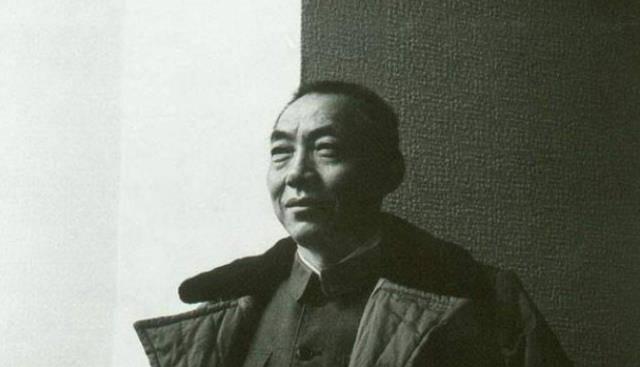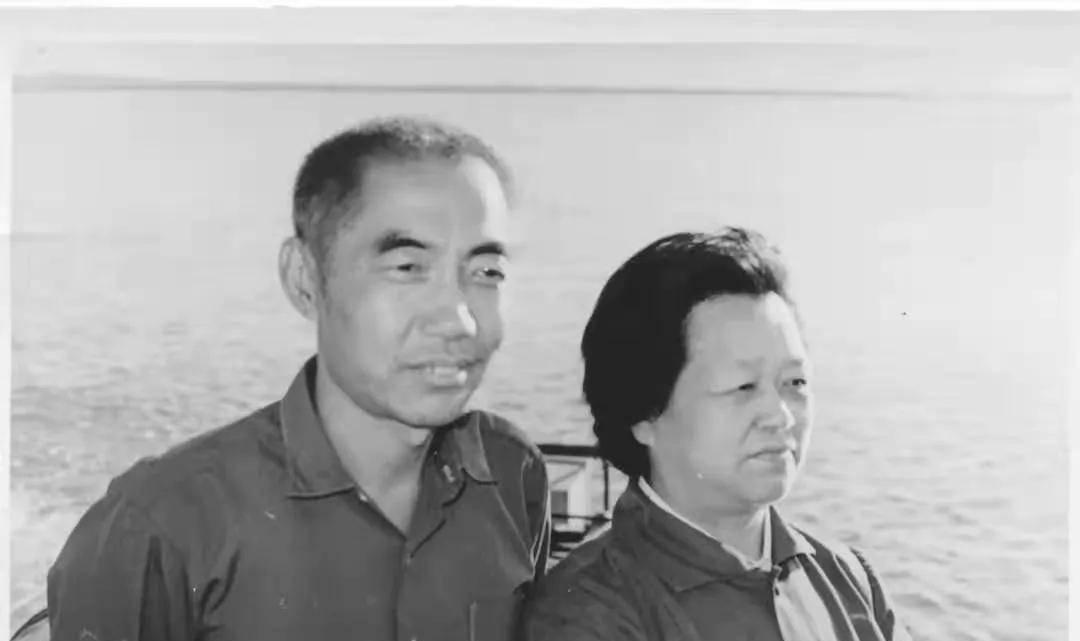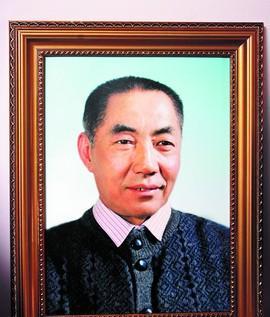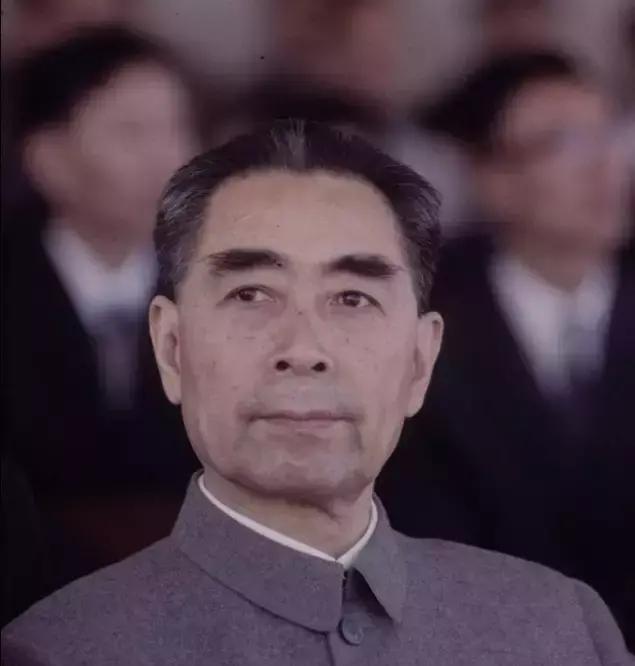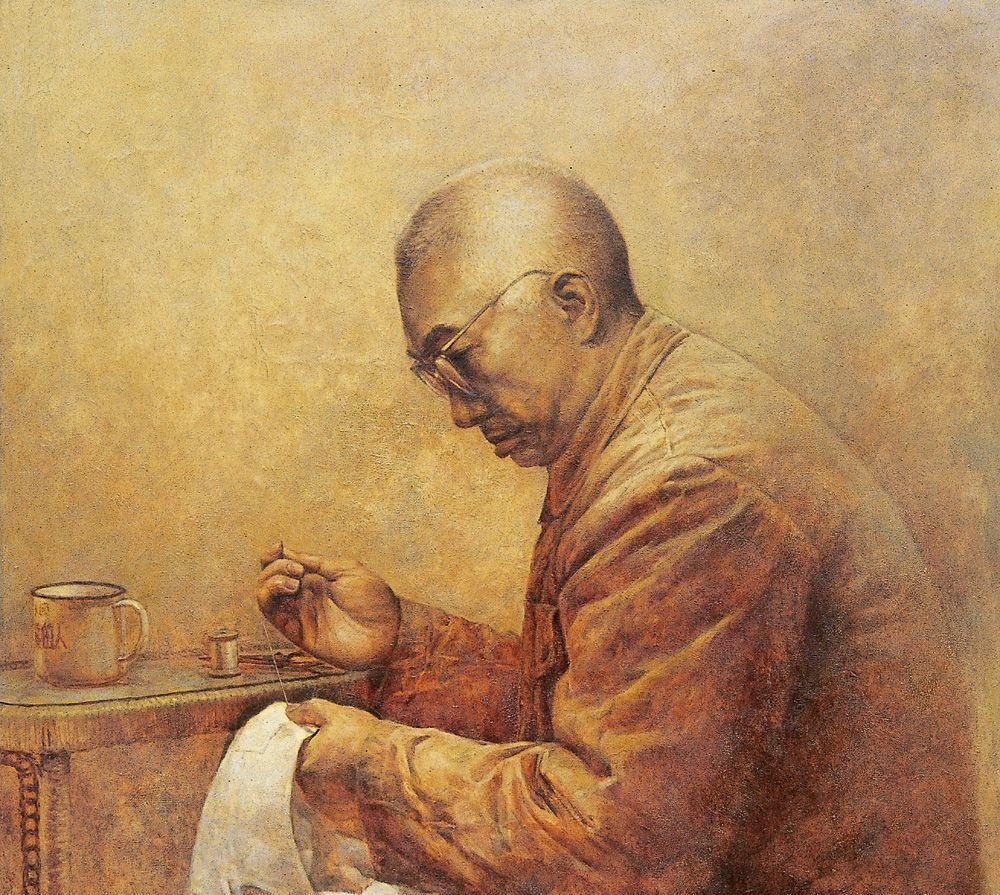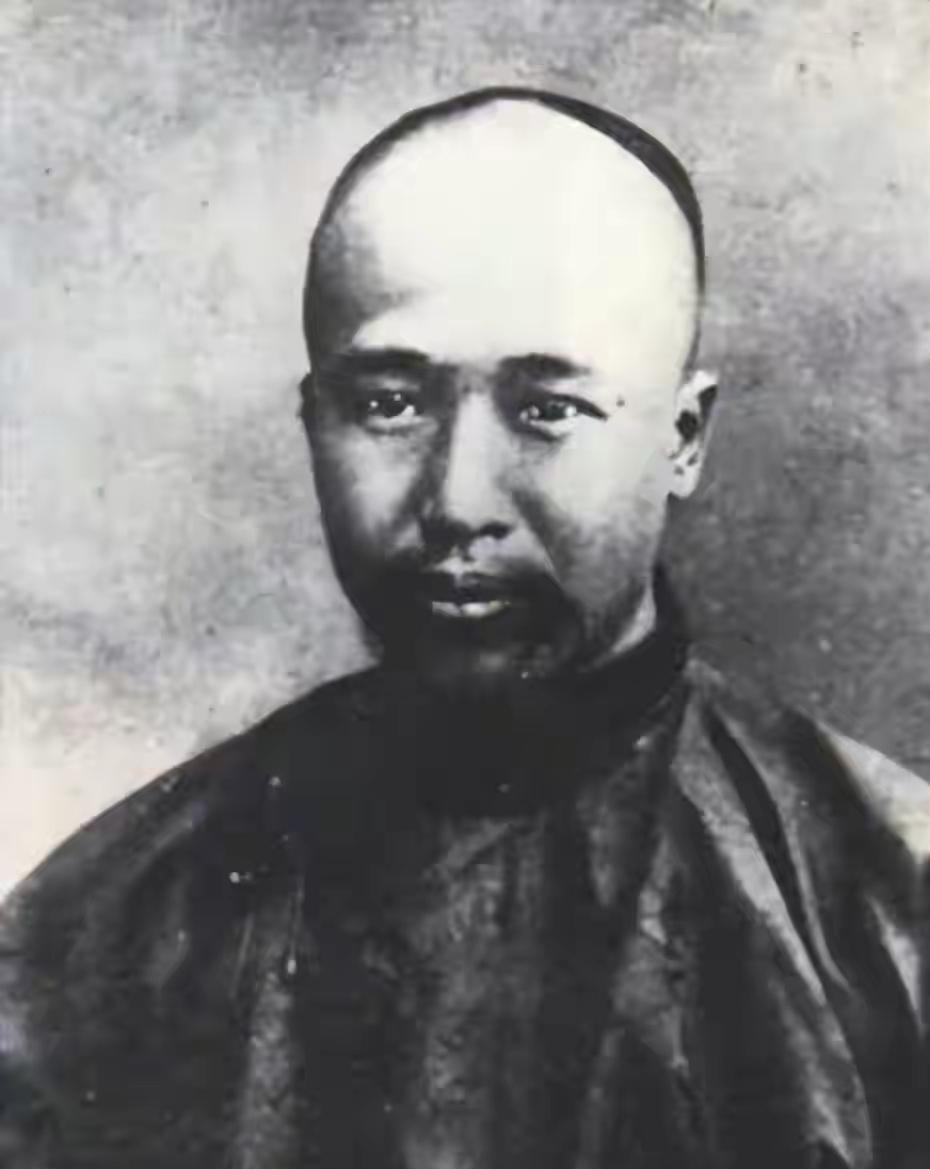实事求是的讲,对浩然的各种批判真的只是针对他的作品吗?笔者认为全盘否定《金光大道》、《艳阳天》,同样是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王蒙也感叹:不了解前三十历史的人,读不懂《艳阳天》,也无法理解浩然!回想“运动”结束后,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评价急转直下。经过最初几年对浩然其人其文的“政治化解读”,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浩然研究重新回归了学术轨道,但此时批评的声音仍然远远大于肯定的声音;对某些作品,如《艳阳天》逐渐形成“定论”,即肯定这部作品对农村生活的描述具有艺术价值,但是阶级斗争的创作理念对作品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 浩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也非常特殊的一位作家。自从1956年发表处女作《喜鹊登枝》至2008年逝世,浩然创作了多部短篇小说和《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等中长篇小说,出版各类作品近千万字,是当代中国文坛高产的作家。而在过去的50多年中,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评价却先后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在20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评论界对浩然的作品整体上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如认为他的作品“朴素、干净,有自然之美”,还有评论者认为浩然的作品能够紧密配合运动和反映当前现实斗争”,因而作品具有“新鲜、明朗、健康、向上”的特征。随着“十年”的到来,主流批评界对浩然的褒奖达到了顶峰。“十年运动”结束后,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评价则急转直下。 在浩然的创作谈中,他多次提及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并直言这种经历对他创作心态和创作情感的深刻影响。他坦言:“作为一个只读过三年半小学,身居僻野山村,连作家名称都不曾听说过的农民子孙,能够爱上写作,能够搞起写作,并以它为终生的职业,如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苦人搞革命,政治上解放,经济上翻身,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运动”后,时代就像一列呼啸前行的列车,带着全新的气息和机遇,浩然紧紧追随着它的脚步,一头扎进了文学创作的浪潮里。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笔耕不辍,创作成果丰硕得让人惊叹。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后续的几年间,他陆续发表了《山水情》《晚霞在燃烧》(1984年)、《苍生》(1987年)等5部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就像一部部厚重的历史画卷,缓缓展开在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百态。 就说《山水情》吧,它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村在时代变迁中的种种变化。故事里的人物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他们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在时代的洪流中努力挣扎、奋斗。有的年轻人怀揣着梦想,想要走出农村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而有的老人则守着那片熟悉的土地,对过去的岁月充满了眷恋。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在讲述故事,更是在反映那个时代农村社会的转型,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晚霞在燃烧》则像是给那些在岁月中逐渐老去的人们写的一首赞歌。它聚焦于老年人的生活,展现了他们在晚年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挑战。有的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孤独寂寞;有的老人身体不好,却还要为生活发愁。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就像那燃烧的晚霞,虽然即将落幕,却依然散发着温暖和光芒。 《苍生》更是将视角放大到了整个农村社会的层面,描绘了农村各阶层人物在时代变革中的命运沉浮。从勤劳朴实的农民到精明能干的村干部,从懵懂无知的孩童到饱经沧桑的老人,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它让我们看到了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既有欢笑,也有泪水;既有希望,也有无奈。 在中篇小说领域,他也塑造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就拿《乡村一个男子汉》来说吧,里面的主人公赵百万是个复员转业军人,有着高大泉式人物的特征,是个公而忘私的乡村干部。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他的态度那叫一个斩钉截铁,和萧长春、高大泉如出一辙。 他常常大声说道:“我不是光为个人,我不是光为老婆孩子!我不是光为自己的小日子……脑袋拴在裤带上打了六年仗,剿了两年匪,为的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为的是中国人都过上好光景!为的是不丢中国人的脸,对得起老祖宗!”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党开口,说我有用处,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枪子儿没打死我,炮弹没炸死我,剩下来的年头日月,全是白拣来的,我还不该把它用在大伙儿的事情上边呀?” 改革开放后,他当上了有名无实的村主任,却依旧认认真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村里有人毁“集体”的树,他立刻站出来制止;有人挖“集体”地里的沙子,他也绝不姑息。别人不理解,果园和土地都承包给个人了,你还管个啥?赵百万却痛心疾首地说:“我是党员,我得维护党的利益,我得维护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呀!我不能装瞎装哑不管哪!”在赵百万几十年的人生中,他经历了上台、下台,挨过处分,蹲过监狱,但他始终无怨无悔,就像一棵深深扎根在土地里的大树,无论风雨如何侵袭,都坚守着自己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