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比较莫言和浩然两位作家,并对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提出批评,认为这两部作品说教意味浓重,且在人性思考层面有所欠缺 。这一观点在文学评论界引发了不少讨论。 莫言作为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其创作风格独特,作品中常融入魔幻现实主义元素,以大胆、细腻且富有深度的笔触挖掘人性的复杂与生活的荒诞。在他的创作理念中,文学应突破单一叙事与简单说教,深入探索人性的幽微之处。因此,当以这样的创作标准与审美视角去观照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时,莫言的批评便有迹可循 。 《艳阳天》以北京近郊东山坞为背景,围绕农业合作社展开故事,旨在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村的阶级斗争,着重刻画了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等先进人物形象。《金光大道》同样聚焦农村合作化运动,讲述农民领袖高大泉带领乡亲们走向集体化的历程。在莫言看来,这两部作品在主题表达上过于依赖直白的宣讲。 例如在《艳阳天》里,为了突出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正确性以及阶级斗争的严峻性,作者常常让人物直接发表大段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言论,像是萧长春在诸多会议场景中,反复强调集体化的好处、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这些话语虽贴合当时的政治语境,但从文学创作角度,使作品沦为了某种政治理念的传声筒,说教意味过于浓烈,打断了故事的自然流畅性,削弱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体验 。 在人性思考方面,莫言认为浩然的这两部作品存在局限。在《艳阳天》与《金光大道》中,人物形象塑造相对单一,多以阶级属性划分人物阵营,正面人物如萧长春、高大泉等,几乎是完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化身,他们大公无私、坚定勇敢,在面对各种困难与挑战时,从不动摇,人性的复杂面被简化;而所谓的反面人物,像《艳阳天》中的马之悦,被塑造成一心破坏集体化、充满私心的反派,其行为动机与性格特征缺乏深度挖掘,仅仅作为衬托正面人物、推动阶级斗争情节的工具存在。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使得作品难以深入到人性的本质层面,无法展现人性在历史变革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 与之对比,莫言在自己的创作中,如《红高粱家族》,塑造的余占鳌等人物,既有勇敢反抗侵略者的一面,又有着草莽的野性与不羁,在道德与欲望之间徘徊挣扎,展现出人性的丰富层次 。 然而,评价文学作品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浩然创作《艳阳天》与《金光大道》时,正值特殊的历史时期,文艺创作肩负着宣传社会主义理念、推动农村集体化进程的使命。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作品带有浓厚时代色彩与说教性有其必然性。 而且,浩然作为农民出身的作家,他试图真实记录那个时代农村的变迁与农民的生活状态,从这一角度,他的作品为研究当时的农村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文学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 莫言对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说教意味与人性思考缺失的批评,从文学创作的艺术标准出发,具有一定合理性,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浩然作品在文学表达上的不足。但我们也应看到,浩然的创作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着独特意义,不能简单地以当下的文学审美标准去全盘否定。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长河中,浩然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存在。他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和鲜明的时代印记,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作品既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又因与政治运动的紧密关联,在不同时代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成为文学界极具争议与话题性的人物。从早期的崭露头角,到特殊时期的声名远扬,再到时代变革后的反思与转变,浩然的文学之路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充满了探索、挣扎与坚守,值得我们深入探寻 。 20 世纪 60 年代初,浩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艳阳天》,这部作品堪称他早期创作的巅峰之作。《艳阳天》全书 126 万字,共分三卷 ,以北京近郊东山坞为故事发生地,聚焦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生动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 小说情节丰富曲折,结构完整紧凑。麦收时节,东山坞不同群体因分红问题产生分歧,土地入社较多的中农、富裕中农希望按土地分配,而劳力较多、土地较少的贫下中农则支持按劳分配,以萧长春、韩百仲为代表的正义力量与以马之悦、马小辫等人为代表的落后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 作品成功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形象。萧长春是新一代农民干部的代表,他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心为公,面对困难和挑战毫不退缩,充满智慧和勇气;弯弯绕则是中农的典型,他精明、自私,有着小富即安的思想,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摇摆不定;马小辫是地主阶级的残余,妄图破坏农业合作社,复辟旧制度,他的形象体现了当时农村中反动势力的存在 。 《艳阳天》不仅人物形象丰满,还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 “艳阳天” 的坚定信念,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1964 年第一卷出版后,迅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浩然也因此家喻户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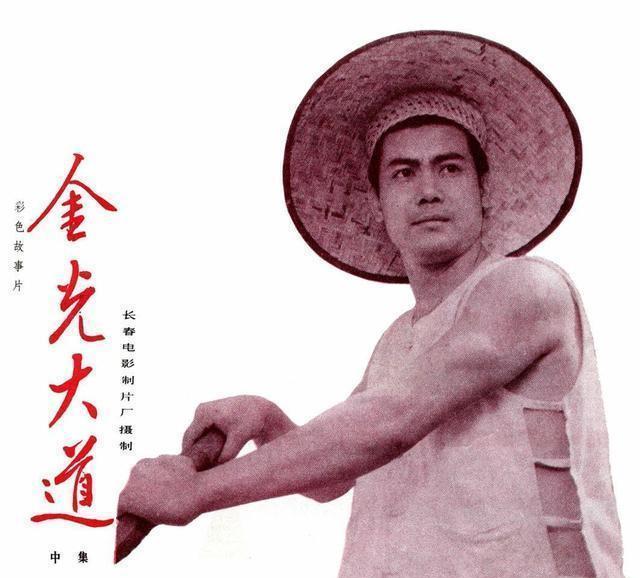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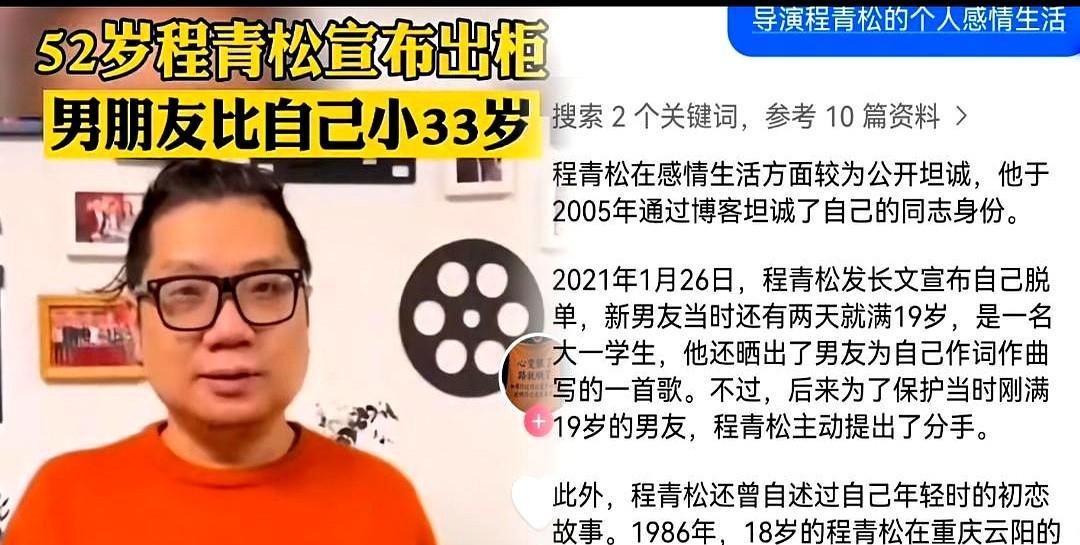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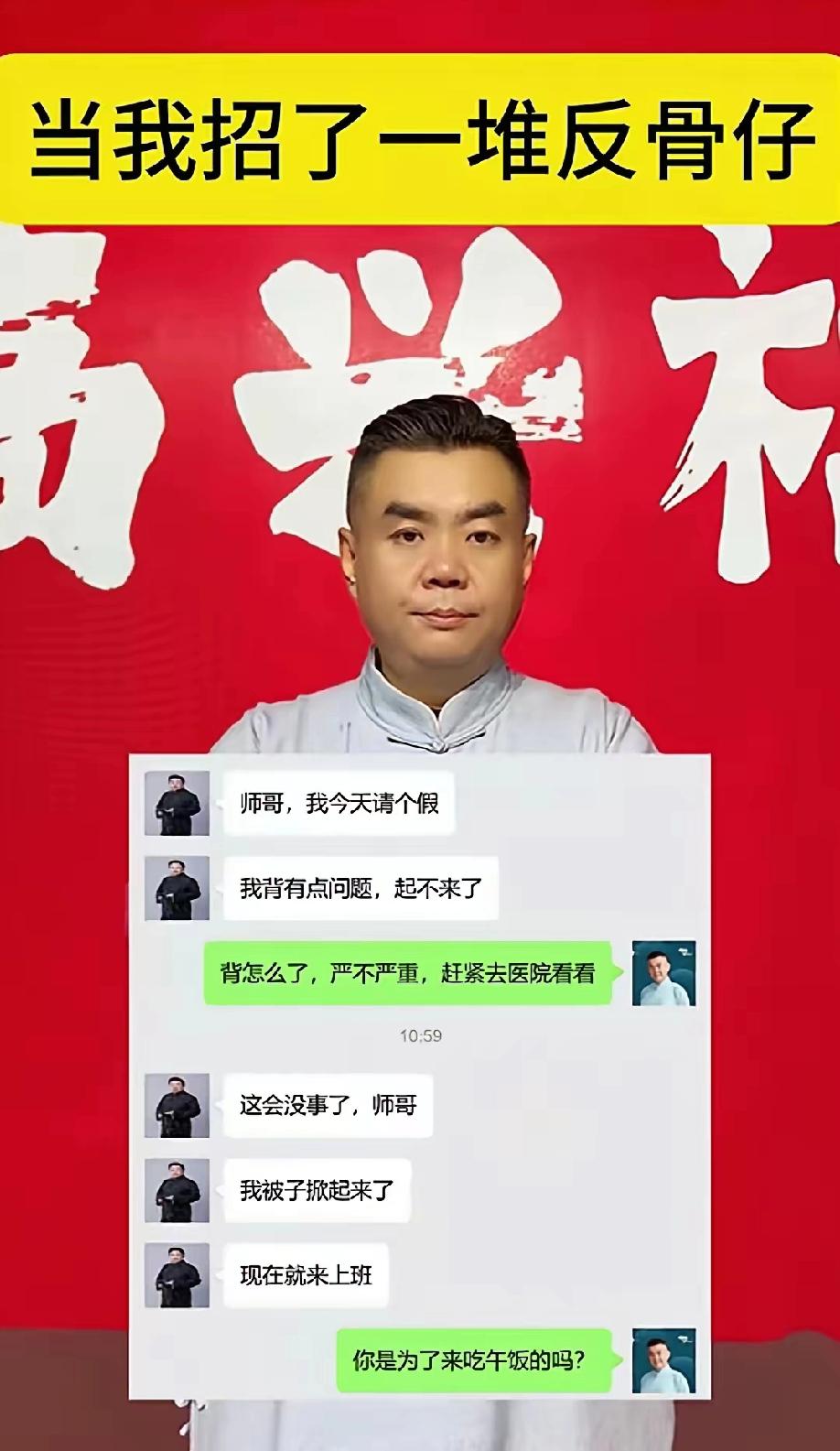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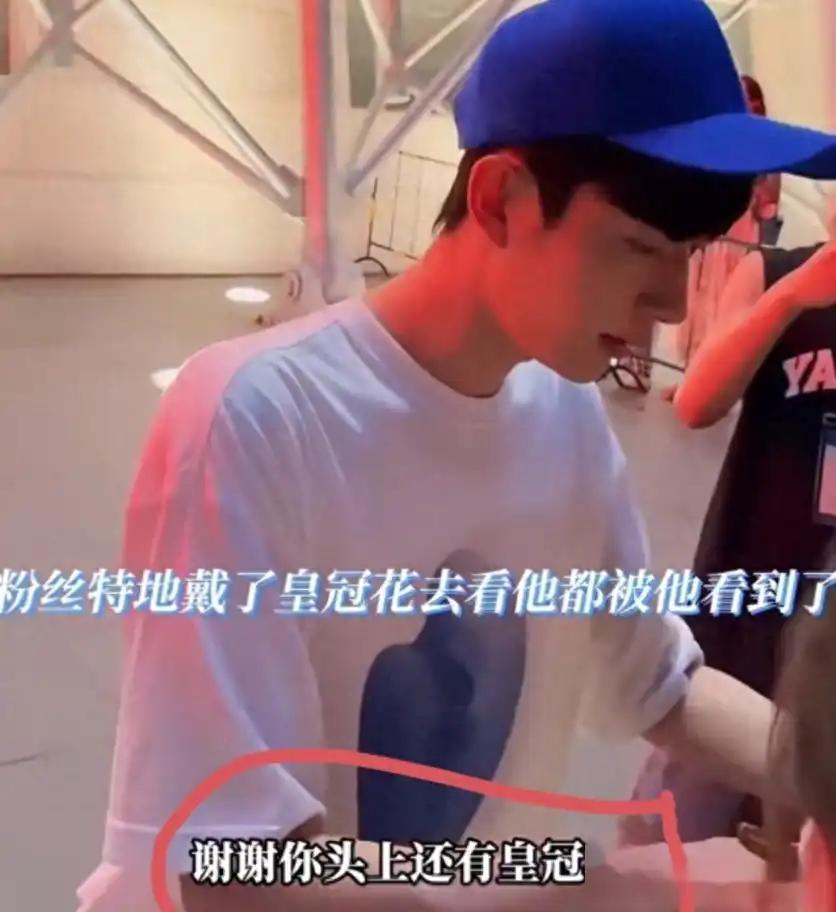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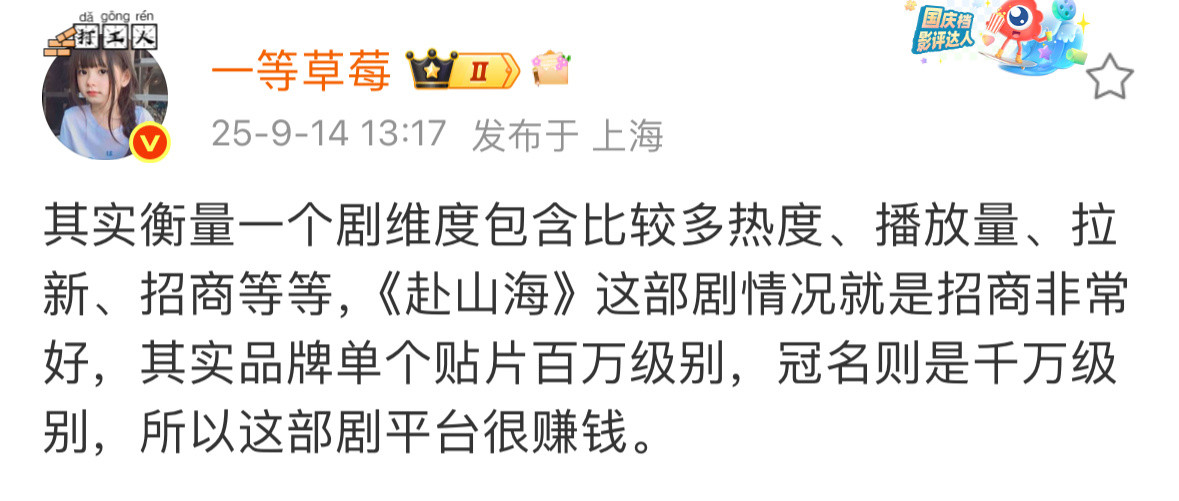

用户97xxx06
莫言与莫迪是一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