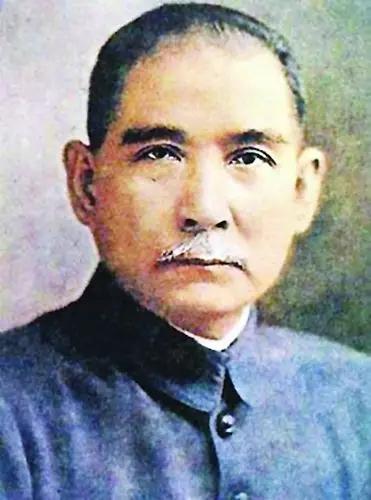1980年,76岁的丁玲,发文痛骂78岁的沈从文:“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沈从文听闻此事,无限悲戚地说:“丁玲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 丁玲与沈从文的交往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那时,他们和胡也频都是怀揣文学理想的青年,因缘际会之下相识并结下了友谊。 有一段时间,三人甚至曾共同居住,一起探讨文学,生活上互相照应。当时他们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沈从文在丁玲和胡也频遇到困难时,曾多次伸出援手。 1931年,胡也频不幸罹难,丁玲陷入悲恸。沈从文始终相伴左右,协助她料理后事。而后,他更是不顾安危,以“丈夫”之名护送丁玲及其幼子返回湖南故乡。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沈从文亦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各方营救。这些早年的情谊和患难与共的经历,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被传为文坛佳话。 然而,两人在文学理念和政治倾向上,其实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丁玲的创作道路越来越与革命斗争相结合,她是一位坚定的左翼作家,其作品和活动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而沈从文则更倾向于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他专注于描绘乡土风情和人性之美,对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根本性的分歧,随着时代浪潮的起伏,为他们日后的嫌隙埋下了伏笔。 1933年沈从文所著的《记丁玲》一书,成为了两人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爆发点。当时沈从文误以为丁玲已经遇害,写作此书的本意是纪念友人。 但丁玲在事隔多年后,尤其是在1979年通过海外版本读到这本书时,感到极大的不满和愤怒。 她对书中关于她个人情感生活的描写方式尤为反感,认为沈从文以“低级趣味”歪曲了她的形象,将她描绘成一个沉溺于个人情感、甚至有些庸俗的女性,这严重玷污了她作为一名革命作家的形象。 丁玲在书的边页上留下了大量批注,言辞激烈地驳斥沈从文的描述。这种被“误解”和“丑化”的感觉,成为了丁玲心中难以解开的心结。 时间来到1980年,此时的丁玲刚刚经历平反,迫切地想要重返文坛并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在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尤其在意自己的革命者形象和历史评价。 或许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当她认为沈从文早年写就的《记丁玲》可能对她构成负面影响时,她选择了公开发文,以非常严厉的措辞批评沈从文。 她不仅指责其作品“胡编乱造”,更将矛头指向其人格,批评他在动荡年代选择退隐是“贪生怕死”,是“市侩”行为。这在当时看来,似乎带有与她所坚持的革命立场进行切割,并划清界限的意味。 面对丁玲突如其来且公开的严厉指责,沈从文感到既错愕又伤心。他并未选择公开撰文回击,而是在私下向亲友表达了自己的委屈与悲戚。 他回顾了早年对丁玲夫妇的种种帮助,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朋友的情分,怎么也没想到晚年会遭到这样的攻击。 沈从文的性格相对温和内敛,晚年已潜心于文物研究,远离文坛纷争。这场风波过后,两人直至去世也未能实现和解。丁玲于1986年去世,沈从文则于1988年离世。 丁玲与沈从文从挚友到决裂的过程,固然有他们性格差异、文学观念分歧以及个人误解的因素,但同样也是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复杂处境的一个缩影。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道路,以及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都在无形中影响着个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恩怨,已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故事,也成为了那段历史中一个值得深思的注脚。它提醒着我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个体的情感、选择和命运,同样值得被关注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