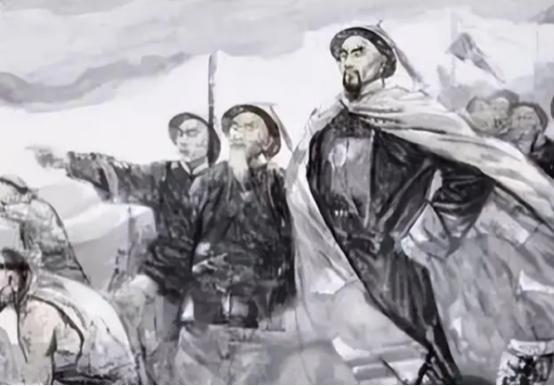1996年,左宗棠曾孙想回上海,写信给市委,请求分一套低楼层的房,谁料,他时任上海副市长的女儿竟毫不犹豫拒绝。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96年春天,重庆一间旧屋的书桌前,八十七岁的左景鉴正小心地摊开信纸,他的手有些颤抖,墨迹在纸上散开微微的晕。 他在信中写道,自己年老体衰,腿脚不便,希望能回到上海,申请一套低楼层的住房,安度晚年,这封信被寄往上海市委,落款处是他苍劲却略显摇晃的签名。 几百公里外的上海,副市长左焕琛在办公室里拆开这封信,那一瞬间,熟悉的笔迹让她心头一紧,办公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她的目光停留在父亲写的几行字上。 她知道父亲从不轻易提要求,也明白政策的界限在哪里,看着那封信,她似乎又回到了很多年前。 1956年的夏天,年轻的左景鉴刚从上海调任重庆,当时他在上海中山医院任职,工作成绩突出,医院刚分配给他一套复式公寓,调令下达时,全家还未搬进去,他沉默了一晚上,第二天便去单位写了退房申请。 女儿那时刚考上医学院,放假后原本可以住在家中,却因为退房只能住在学校宿舍,左景鉴叮嘱家人,房子是国家的,若自己离开,就不应占着不放,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像在陈述一件必须完成的事。 他带着妻子去了重庆,从此在那座山城扎根四十年,到任后,他每天早出晚归,在病房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那时医疗条件艰苦,他常在昏黄的灯下对着外文资料做笔记,研究适合当地患者的手术方法。 腹部外科的手术器械短缺,他就自己改造工具,那把如今陈列在纪念室里的手术刀,刀柄因长期使用而发亮。 他在工作中立下三条规矩,不用昂贵的进口药,不收患者红包,不接私活,有人术后塞给他一个信封,他当场交给医院党组织,并写了说明。 这些年来,他几乎没有休息过,房子漏雨,他自己动手修补;冬天冷得睡不着,他就披着大衣读资料。 有人问他为何不调回条件更好的地方,他只说这里需要医生,时间在病房与手术灯下流逝,等到头发花白,他才真正有了“想回上海”的念头。 1996年写信那天,他用的是老旧的钢笔,信中没有一句请求照顾的字眼,只写明自己的情况与希望,他仍像年轻时那样守着规矩,相信事情可以“按程序办”,信寄出后,他并未多想,只让人帮忙查查邮路是否通畅。 左焕琛收到信后,沉默了很久,她早已知道父亲的身体状况,但手边摊开的政策册子提醒她,住房分配有明确规定。 她在那一页上画线,在信纸上写下回信:父亲不在上海工作,不符合分房条件,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字迹刚劲有力,她写完后停顿片刻,把信装入信封,当天下午,信寄往重庆。 几周后,左景鉴收到了女儿的回信,他坐在窗边,慢慢拆开,看完后,他笑了笑,让人拿来宣纸,用颤抖的手写下八个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他明白女儿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也明白自己这一生所坚持的信念并未断层。 一年后,他离开了人世,女儿遵照遗愿,将骨灰撒入长江,那是他一生行医的地方,也是他心心念念要回的故乡的方向,江水滚滚,他的名字随波而逝,却留下了一段传承。 多年以后,重庆街道办在旧医院旁建立了一间纪念室,展柜里摆着他的手术刀、退房申请和那封回信,人们经过时,总会停下脚步,工作人员说,这些东西看似平常,却能让人看见一个家族的脊梁。 左焕琛已年过八十,她退休后仍穿着白大褂在社区义诊,怀里常带着父亲留下的旧怀表,表针的滴答声在她耳边回响,每当有人问起那封信,她只是微笑,说那是家风的回音。 从左宗棠到左景鉴,再到左焕琛,百年间的左家没有留下丰厚的财富,也没有辉煌的宅邸,只留下几页纸、一把刀和几句朴素的道理。 那封信,不仅是一位父亲的请求,更是一种传递:无论时代怎样变,规矩、公心、公正,始终是家中最重要的传承。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世纪》杂志 |晚清名臣左宗棠曾孙、外科专家左景鉴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