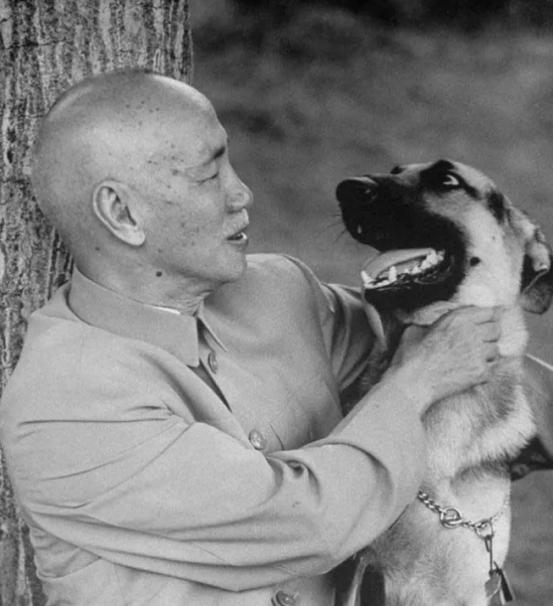1975年,蒋介石在台北去世,说来也巧,蒋去世的那天正好是清明节,早上的时候都还好好的,到了晚上突然不舒服,医院的医护人员们也是积极抢救,但此时的蒋已经油尽灯枯,没多久蒋永远的闭上了双眼。 1975年清明那天,台北下了整整一天的雨。 天不响,也不亮,湿气透人。早上起来,街头店铺没开几家,广播里一遍遍放着老曲子。士林官邸那边,灯亮了一宿,外面围着几层卫兵,没人多说一句话。 屋子里,医生守着,护士不敢喘气。 蒋介石躺在床上,脸色泛白,嘴唇几次动了动,说不出完整的话。他身边那几个人,手里拿着速写本,全盯着机器上的曲线。 到了晚上十一点五十分,曲线拉平了,谁也没喊,过了一会儿才有人走出去,雨还在下。 消息没立刻公布。 过了几个小时,“中央社”才发了短稿,说“蒋总统已于昨日晚间病逝”。 整个台湾一早都在听广播。司机停在路边,摊贩没出摊,校车也少了一半。国民党中央临时开会,严家淦主持,宣布降半旗,全台哀悼,治丧委员会立刻成立。 几张蒋的照片被挂出来,全是穿军装、站得直的那种,黑框,白底。有人哭,有人不出声。马路上开始贴白纸,电台播的音乐都慢了半拍。台北的天,还是没放晴。 当晚治丧办公室开了长会,连夜调档、挑灵堂布置,连蒋自己留下的交代都翻出来。 里面最让人琢磨的一条是,他要求死后穿七条裤子。 最初没人信,以为秘书写错了。可查了他在日记里的旧话,确实提过:“人归故土,要穿全。”老家在浙江宁波溪口,那里有个习俗,人死要穿七件衣服。 下葬时讲究“七重”,外人听着怪,其实是一种念旧。 蒋晚年常念家乡,说那里的雨比台北细,山也不那么高。他屋子里一直挂着一幅溪口的山图,是他自己画的,手抖,但线条认真。 他在岛上活了二十多年,到死也没再回去,恐怕心里清楚,这辈子是回不去了。 遗体先停在官邸,随后移往国父纪念馆,设灵堂。 黑纱挂满墙,花圈摆得整整齐齐。老兵带着勋章前来吊唁,有人穿着旧制服,说话哽咽。 美国那边动作快,总统福特发来唁电,副总统洛克菲勒亲自出席丧礼。日本也派了政要。外国记者都到了,争着拍照。治丧程序写得细,谁站哪一排,谁先鞠躬,全有顺序。 那场葬礼,其实已经不是单纯送一个人走了,更像是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时代真结束了。 而另一边,北京的反应简单得很。 4月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右下角发了一条短讯:“蒋介石死了。”没照片、没引语。 新华社稿件照发,没有改动。 字眼不偏不倚,时间写清楚,地点也没错,但一字不多,一句不补。当时看到这则消息的人,大多是翻到那一页时,眉头皱一下,然后继续看别的新闻。 蒋的死讯传到中南海的时候,天还没黑。 说话的人小声汇报,说蒋介石走了。 毛主席当时正看文件,抬头望了一下,说了三个字:“知道了。”语气平,没有起伏,也没继续说下去。传话人退了出去,屋里一会儿没声,只听得见窗外风刮树叶的声音。 那三个字,后来被很多人传来传去,但没人能确证是不是原话。文件里没写,记录也没留。可奇怪的是,很多人信。 蒋和毛,关系太复杂了。 抗战时,两个党勉强合作,一个做统帅,一个扛宣传。 见过面,也交过手。重庆谈判那年,两人坐在一起拍了照。照片里气氛不热,笑也僵。 接下来几年,形势变了。 内战开打,蒋退往台湾,毛在天安门建国。从那以后,谁也没再主动提起过对方。 毛主席在一些内部讲话里提过,“蒋也是中国人。”话不多,但点到为止。 他没公开批蒋,也没替他说话,只是淡淡地放在那儿。其实那时候,他的身体也不太好了,说话慢,走路需要人扶。有人记得,那天听到消息后,他坐了一会儿,然后继续翻资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蒋的晚年日记,有不少已经公开。 能看出来,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日记里写得不多,大多是身体状况、时政安排,还有一些旧事碎片。他偶尔提起大陆,说梦见家乡,说“梦里下了雪,屋檐结冰”。他老得慢,也撑得久,靠药物维持,靠念书打发时间。 到头来,留下的不过几句话,一段病历,一身老衣裳。 毛主席那几年也老了。 讲话带喘,说话得断句。身边的人记得,他有时候看旧照片会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没有写下任何与蒋介石相关的文字,也没给中央发指示。 整件事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不激起水花,只留下点湿痕。 后来有学者说,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蒋介石的灵柩后被安放在大溪陵园。 陵园选得安静,四周种满松树,来的人不多。有人说那儿风大,落叶常年不断。 墓碑很简洁,没有多余的碑文,只写了名字和生卒。有老兵常来站一会儿,不说话。也有游客偶尔经过,拍张照,走了。 时间过去了多年。档案被解封,回忆录出版,学者出书,纪录片拍了一部又一部。 可那天晚上,台北的雨声、中南海的灯光、那句“知道了”,都没变。就那么静静放着,像一张旧照片,角上有点卷,也没人敢扔。







![当年,只有蒋介石感受到了我党的强大,各大军阀还在沾沾自喜。[滑稽笑][笑而不语](http://image.uczzd.cn/17399233488999652282.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