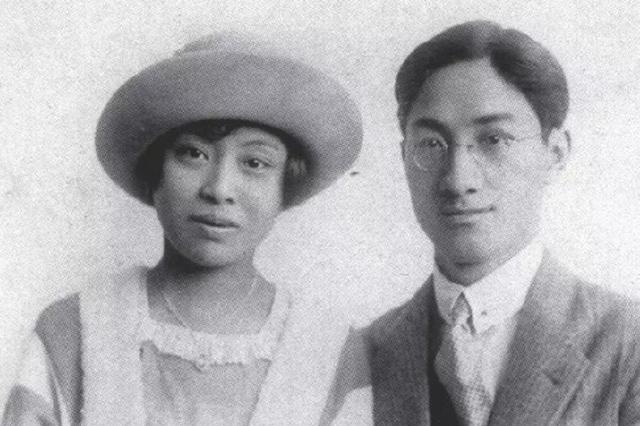1932年,在徐志摩的葬礼上,陆小曼坚持要将徐志摩的寿衣换成西装。有人小声告诉她说:“她来过了,不让换。”陆小曼抖着唇想再说什么,可终究没说出来。 咱得先搞明白,陆小曼为什么非要换西装? 这事发生在1932年5月,徐志摩在1931年11月飞机失事,已经过去了足足半年。在上海的公祭日上,陆小曼看着灵柩里的丈夫,彻底崩溃了。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丝袍寿衣。在陆小曼眼里,这太陌生了。 她要的是她记忆里的那个徐志摩。是那个穿着笔挺西装、风度翩翩的诗人;是那个在舞会上领着她跳舞、在月下为她念诗的“摩”。那身黑丝袍,像一个冰冷的符号,提醒她,她的爱人已经彻底成了“故人”。 说白了,陆小曼是个活在极致浪漫里的人。她的爱是浓烈的、是占有的。她无法接受一个“中式”的、“传统”的徐志摩走向死亡。她坚持换上西装,是想用这种方式抓住最后一丝她熟悉的感觉。她要让徐志摩以她最爱的样子离开。 在她的逻辑里,这要求合情合理。她是遗孀,她有权决定丈夫的最后体面。 可她忘了,她面对的,是张幼仪。 就在陆小曼坚持要“亲自动手”换衣服,场面快失控时,张幼仪的朋友赶紧给她打了通电话,吼着让她必须来一趟。 张幼仪本人压根没打算出席。她不想见陆小曼。但一听这事,她还是穿着黑旗袍赶到了。 她只看了一眼灵柩,就明白了。晚年她在回忆录里提过当时的心情,翻译过来就是:她觉得恶心。 这种“恶心”,不是对陆小曼,而是对“折腾遗体”这件事。 咱得知道个史实:徐志摩是飞机失事,撞山死的。遗体受损极其严重,是经过了缝合处理的。而且,这都过去半年了,遗体是经过防腐保存的。 张幼仪是个极其务实的人。她想的是:“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再承受更多折磨?” 在张幼仪看来,陆小曼的“浪漫”要求,简直就是对死者最后的“折磨”。让一个破碎并保存了半年的遗体,再经历一次“换装”,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当朋友问她怎么办时,张幼仪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只要告诉陆小曼,我说不行就好了。” 她甚至都没进那个房间,没和陆小曼当面对质。她知道,她不需要。 最有意思的,就是传话人那句:“她来过了,不让换。” 陆小曼一听,嘴唇抖了抖,最后没敢再闹。为什么? 这一刻,陆小曼悲哀地发现,她才是徐家实际上的女主人。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从头到尾就没认过陆小曼这个儿媳。他嫌她败家,嫌她抽鸦片,嫌她让儿子“性情浮躁”。在徐家二老眼里,那个“乡下的土包子”张幼仪,才是他们唯一的儿媳。 徐志摩的母亲去世时,张幼仪已经离婚多年,却还是被徐家请回去,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丧葬事宜。 这次徐志摩的后事,更是张幼仪派自己的八弟张禹九和儿子徐积锴去收的尸。那副形状像树干一样的中式寿板,也是张幼仪弟弟操办的。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庇护。 她背负着“克夫”和“败家”的骂名。所有人都把徐志摩的死,归结到了她的挥霍无度上。要不是她花钱如流水,徐志摩至于为了省钱,去搭乘那架免费的邮政飞机吗? 陆小曼在葬礼上,是悲痛,也是孤立无援。她连最后一点“任性”的资格都没有。她想为丈夫换件衣服,都得看那个她丈夫当年拼命抛弃的女人的脸色。 她没说出来的话,是她的委屈,也是她地位的尴尬。 这件“寿衣之争”,活脱脱展现了两个女人对徐志摩截然不同的爱。 陆小曼的爱,是烈火。她要的是爱情本身,是激情,是浪漫。她爱的是“她的摩”。所以徐志摩死了,她也要他维持着“她的摩”的样子。 这种爱很炙热,也很自私。她只考虑自己的感受,没想过遗体的实际情况。 而张幼仪的爱,是大地。她被抛弃,却活成了徐家最坚实的后盾。她的爱,是责任,是成全,是体面。 她不爱徐志摩这个人吗?未必。她为徐志摩守着父母,养大孩子。她晚年还说:“他才35岁,那么年轻,又那么有才气,哎!”这里面有惋惜,有复杂的情感。 但她更懂“尊重”。她要守护的,是“徐志摩”这个人的最后尊严,是徐家的体面。 所以你看后来的结局: 陆小曼守着徐志摩的遗像,和翁瑞午同居了三十多年。卧室里挂着徐志摩的遗像,这是她纪念爱情的方式。她也想整理徐志摩的文稿,但困难重重,终未做成。 而张幼仪,这个被徐志摩嘲讽的女人,转身投入商海,成了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的副总裁,开了“云裳”时装公司。她把徐志摩的儿子培养成才,给徐家父母养老送终。 最后,还是张幼仪,主持编辑出版了最全版本的《徐志摩全集》。 一个保留了他的画像,一个保留了他的灵魂。 陆小曼赢了徐志摩生前的爱,却在葬礼上输掉了最后的体面。张幼仪输掉了婚姻,却在徐志摩死后,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包括徐志摩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