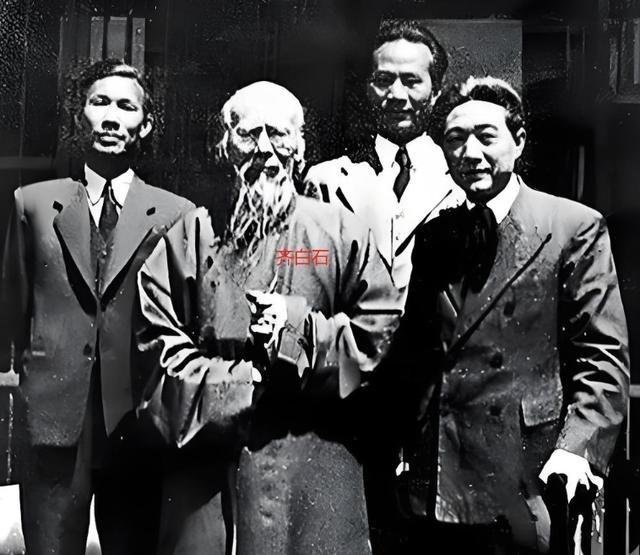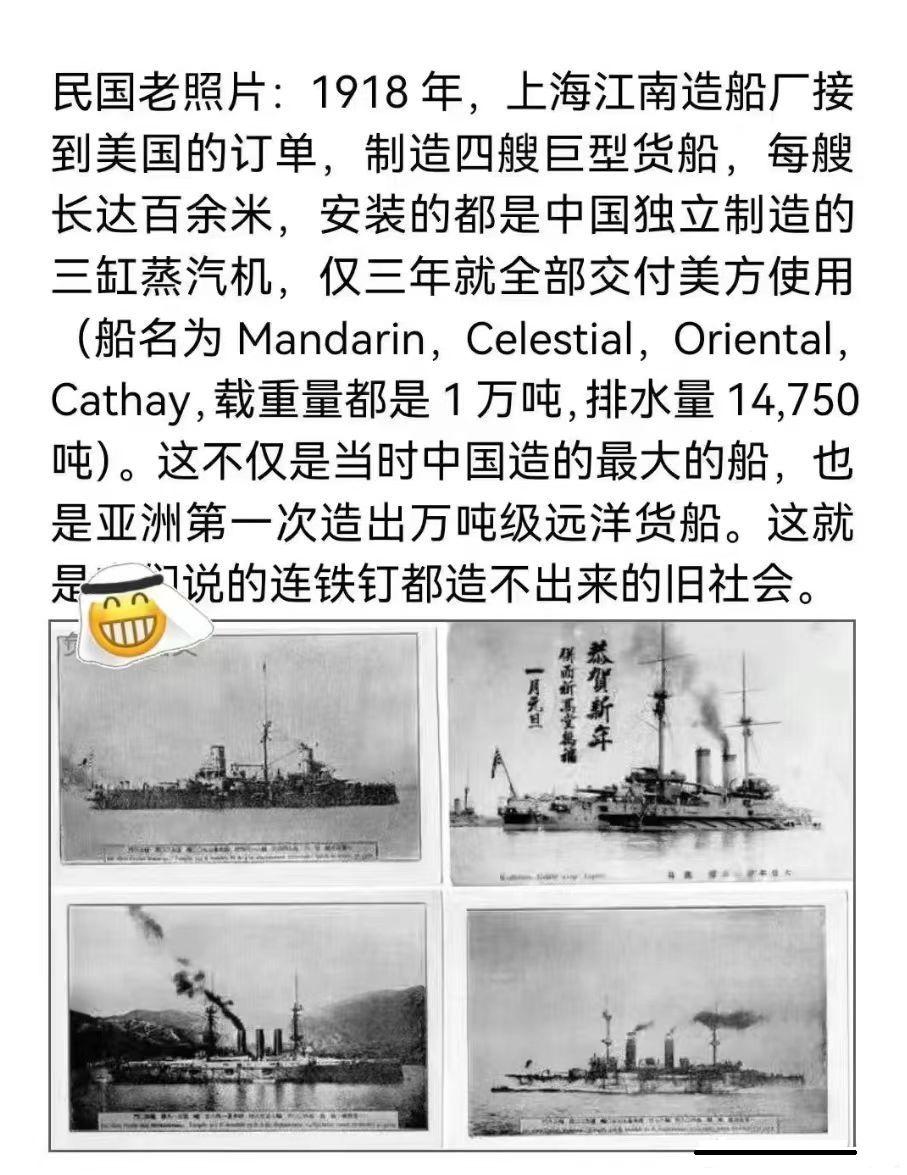1926年,齐白石在北京购置了一四合院,想要找一个看门人。一个晚清老太监主动上门,提出:“我不要一份工钱,免费帮你看门。” 老太监无怨无悔干了20多年,临辞前提出:“能否给我几幅画做留个纪念?” 齐白石生在1864年的湖南湘潭杏子坞,家里穷得叮当响,长孙一个,八岁读了半年私塾就回家放牛砍柴。田里干活时,他常用树枝在地上画牛画鸡。十四岁学粗木匠,十五岁转雕花,刀工练得飞起,乡里人抢着请他做家具。二十岁左右开始认真学画,先跟当地文人学工笔草虫,再拜胡沁园、王闿运这些大师学诗文书法篆刻。三十多岁已经在湖南小有名气,五次远游西安、北京、广西,见了世面,画风越来越活。 1919年,57岁的他带着一家子第七次来北京,这次是铁了心扎根。头几年租房子住,卖画糊口,北京画坛老派看不上他那股乡土劲儿,有人当面骂俗气。他不争,闷头画。陈师曾把他的画带去日本展出,一下子炸了锅,日本人不惜重金抢购,巴黎艺术大会也选了他的画。从那以后,齐白石在北京站稳脚跟,画价一天一个样。1926年冬天,他攒够钱,在西城跨车胡同15号买下带跨院的小四合院,终于有个固定窝,能安心画画了。 这个院子不大,三间北屋带铁栅栏,成了他的画室。南边空地他自己种丝瓜南瓜葡萄,边种边写生。买院子那年他62岁,正好父母双亡,回不去湖南奔丧,只能北京设灵守孝。院子买下后,求画的人更多了,三教九流都来,门槛都快踩烂。他不善拒绝,画案前时间被挤得没剩多少,只好贴告示招看门人,要找个眼力见儿好、嘴皮子利索的,能把闲人挡在外头。 应征的人不少,大多想借机偷学两手,齐白石一看就摇头。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个瘦瘦的老头自己找上门,自称尹春如,原是清宫太监,后来分到肃王府当差,王朝没了就流落街头。尹春如说自己孤身一人,只要管饭就行,不要工钱。齐白石起初犯嘀咕,但看他举止得体,就留下来试试。尹春如上手特别快,早起扫院,客人来先问清楚来意,真心爱画的才放行,不想见的就客客气气挡回去,从不让人下不来台。 齐白石看他干得漂亮,每月画几张虾蟹蔬果给他当工钱。尹春如收画小心收藏,有些卖给真正懂行的收藏家,日子渐渐宽裕。抗日那几年,北京城乱,日本人听说齐白石名气大,常派人上门要画。齐白石不愿合作,又怕硬顶出事,尹春如就挂大锁,贴告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卖画的事交给南纸店办。那些告示后来尹春如都揭下来自己收着。二十多年过去,尹春如从五十多岁干到七十多岁,把齐白石从人情琐事里彻底解放出来,让他专心创作出无数精品。 1940年代末,尹春如腿脚不好了,觉得拖累主人,就提出回天津养老。齐白石想给一笔钱,他死活不要,只说跟了先生这么多年,能不能再画几幅留个念想。齐白石当场铺纸,画了好几张大虾大蟹,题款盖章,全送给他。两人道别,尹春如带着画回天津。1957年齐白石去世,国家要建纪念馆,尹春如听说后,从天津赶来,把自己攒了二十多年的几十幅齐白石精品全捐了,一张没留。他说这些画本来就该让大家看。 尹春如晚年在天津小屋里度过,没儿没女,墙上空空荡荡,却过得踏实。齐白石的跨车胡同老院子,现在还留着那道铁栅栏大门,尹春如守过的门槛,静静立在胡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