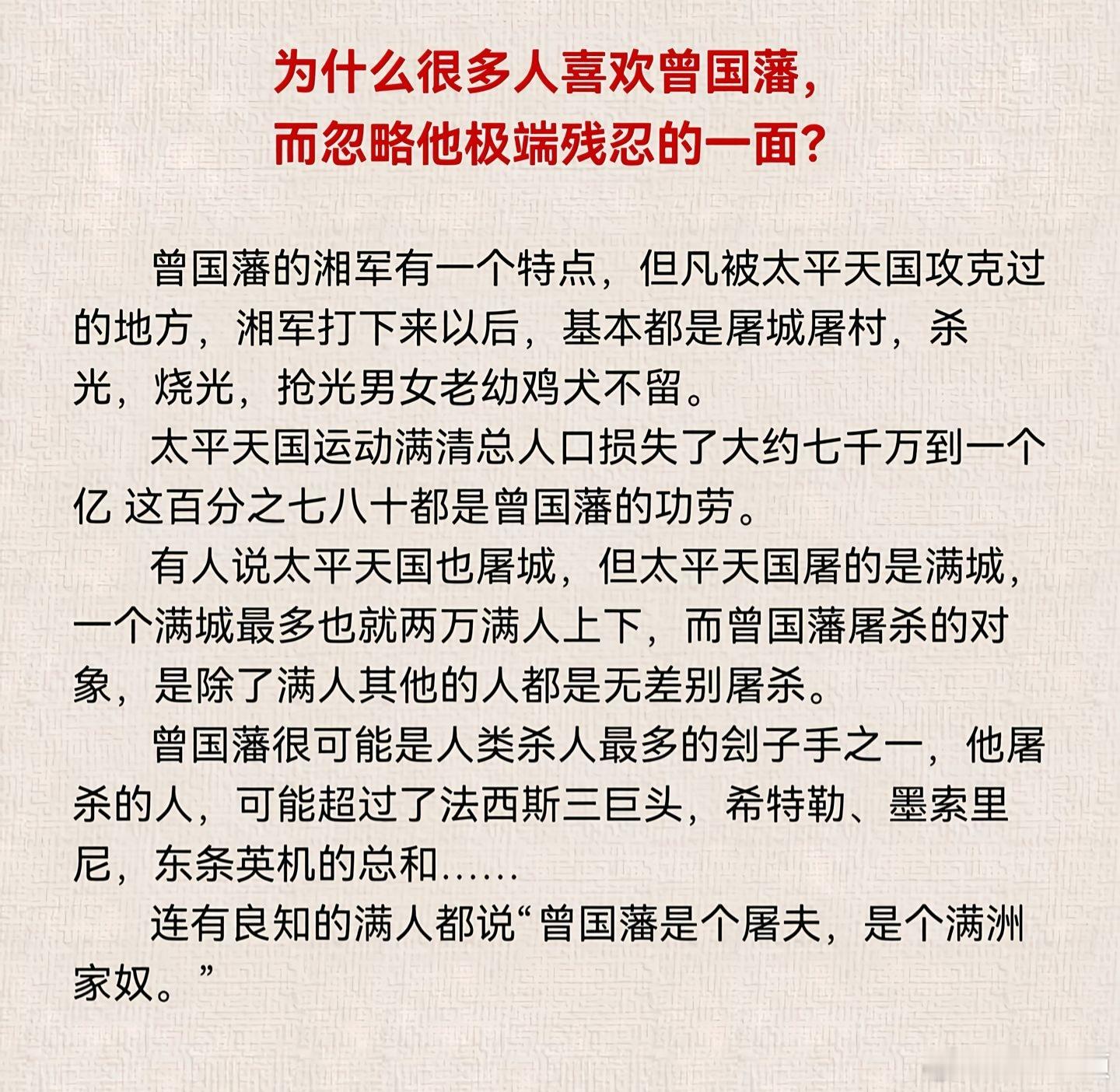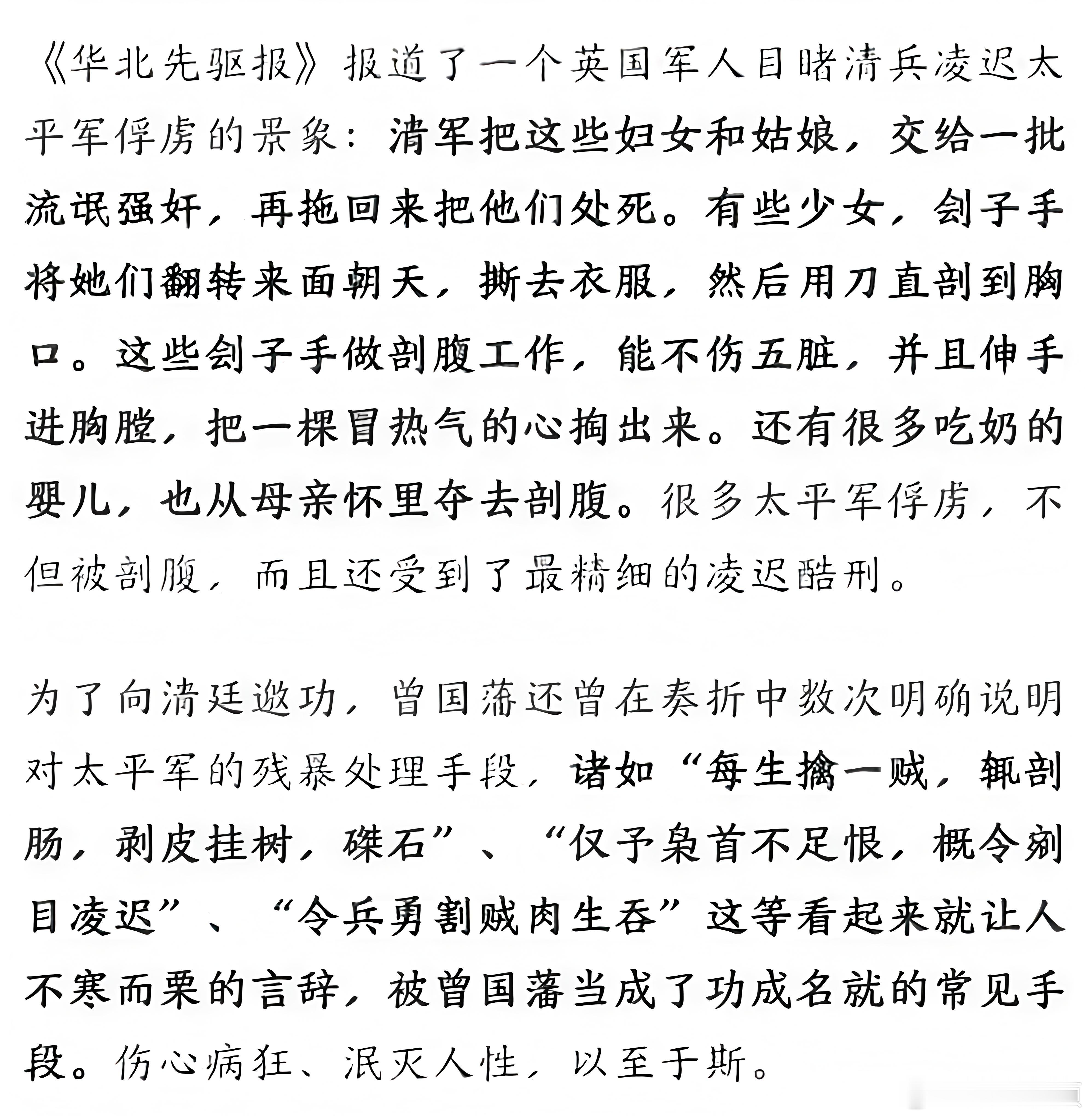曾国藩: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会跟这九种人深交,以免惹祸上身。 第一种不可深交的,是好占便宜、贪小失大者。早年曾国藩初入京城为官,月薪仅四两银子,同乡中有人总以家眷患病为由借钱,转头却在琉璃厂挥霍淘字画。曾国藩拮据时委婉提及还款,对方竟反唇相讥,指责他读书迂腐、不顾情面。 后来太平军围城,此人率先投靠伪政权,临刑前仍在喊冤,全然忘了昔日受助之恩。湘军初建时,帐下文书陈升写得一手好字,却在抄录军报时私扣阵亡将士三成抚恤银,美其名曰“办公损耗”。曾国藩虽未当即处置,却早已将其归入不可用之列,果不其然,三个月后陈升私刻关防卷款潜逃,最终被太平军乱刀砍死在湘江河畔。曾国藩在日记中批注:“贪小利者必忘大义,与其缠斗,不如早离,免生祸端。” 第二种是恩怨颠倒、是非不分者。同治元年安庆城稳定后,曾国藩曾向幕僚提及早年在长沙办团练的经历。当时参将李迪庵曾因军纪问题被他当众训斥,后李迪庵战死三河,其弟竟跪在辕门外大肆谩骂,称“曾剃头害死我兄”。可此人全然忘却,当年其母病重时,是曾国藩垫付汤药费,也是曾国藩保荐李迪庵从把总一路升至副将。这类人心底无秤,不分好歹,你对他的恩惠转瞬即忘,稍有不满便会反目成仇。曾国藩深知,与这类人相交,非但得不到回报,反而可能被倒打一耙,徒增无谓的麻烦。 第三种是阿谀奉承、口蜜腹剑者。晚清官场盛行趋炎附势之风,曾国藩对此极为警惕。他曾遇到过这样的幕宾,专挑上司喜好说话,对决策中的疏漏视而不见,满口奉承之词,转头却在背后散布流言、窃取机密。同治三年的一场朝会,有御史突然弹劾曾国藩“拥兵自重”,言辞激烈,事后查明,此人正是当年在江西赈灾时因私扣粮款被曾国藩罢免的县令,如今攀附新贵,专程前来寻仇。这类人眼中唯有利益,奉承是为了索取,一旦目的未达或反目,便会不择手段构陷,远比明枪易躲的对手更危险。 第四种是落井下石、见利忘义者。曾国藩认为,人在顺境时交友易,逆境时方能见人心。咸丰七年,他在荷叶塘守制期间,因父亲去世、战事不利双重打击,一度陷入低谷,不少昔日往来密切的官员、同乡纷纷避之不及,更有甚者趁机散布他“治军无方”的谣言,试图踩着他向上攀爬。相反,那些真正的益友,即便自身难保,也会送来书信慰藉。这让他愈发坚定,落井下石者不可交,他们今日能在你落魄时幸灾乐祸,明日便可能为了利益出卖盟友,与这类人相交,无异于养虎为患。 第五种是志不同道不合者。曾国藩一生秉持“经世致用”的理念,全力推进洋务运动,力求挽救晚清危局,因此对思想顽固、胸无大志的迂腐之人避之不及。早年在长沙书院求学时,他曾与几位同窗交往,这些人沉迷科举八股,鄙视实务,动辄宣称“读书无用,唯有功名可贵”,对西方先进技术更是嗤之以鼻。曾国藩与之辩论数次后便不再往来,他深知,道不同不相为谋,与志不同者强合,只会被其狭隘眼界拖累,消磨进取之心,甚至在关键决策上产生分歧,引发祸端。 第六种是不孝不悌、德行有亏者。曾国藩始终坚信“百善孝为先”,认为一个人若连至亲都不尊重善待,更难真心对待他人。在两江总督任上,他曾遇到一位武弁,作战尚可,却长期克扣母亲的医药费,甚至对兄弟拳脚相加。曾国藩得知后,当即拒绝了其升职的请求,即便有人说情也不为所动。他深知,德行是立身之本,不孝不悌者往往自私自利,毫无底线,与这类人共事,迟早会因其品行缺陷牵连自身。 第七种是优柔寡断、全无主见者。军旅生涯中,曾国藩深刻体会到,关键时刻的决断力直接关乎成败,因此绝不与毫无主见、人云亦云者深交共事。有次攻打太平军据点,一位将领因过度犹豫,错失攻城良机,导致湘军损失惨重。事后曾国藩查明,这位将领凡事都要听从他人意见,毫无自己的判断,遇到风险便畏缩不前。这类人不仅难以成大事,还会在危急时刻拖累团队,引发连锁灾祸。 第八种是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者。曾国藩交友极重诚信,认为“人无信不立”。早年他曾资助一位同乡赴京赶考,对方承诺考中后归还银两,结果高中后却绝口不提,甚至谎称从未借过钱。后来此人因贪腐被查处,曾国藩毫不意外。他深知,反复无常、言而无信者,毫无契约精神,与之相交,随时可能被其背叛,无论是财物往来还是事业合作,都暗藏风险。 第九种是德薄量小、嫉贤妒能者。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他始终鼓励下属各展其长,因此对嫉贤妒能、心胸狭隘者尤为警惕。有位幕僚见李鸿章才华出众,深得曾国藩器重,便暗中散布李鸿章的谣言,甚至在起草文书时故意篡改内容,试图破坏李鸿章的差事。曾国藩察觉后,当即将其辞退。他明白,德薄量小者见不得他人好,会因嫉妒心生歹念,暗中使绊子,不仅会破坏团队氛围,还可能引发内部纷争,动摇成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