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东莞市殡仪馆内送来了一具已经有味道的女尸,火化工人何亚胜经过火化车间,突然看到一具无名女尸的肚子似乎在微微地起伏! 三伏天的殡仪馆车间像个密不透风的铁盒子,福尔马林的气味混着腐味往鼻腔里钻。 何亚胜推着手推车经过停尸台,眼角余光扫过那具盖着白布的躯体——刚才明明看到白布下的肚子,像漏风的风箱似的,轻轻鼓了一下。 同事催他赶紧处理下一具,他却蹲下身,伸手掀开了白布一角。 那张脸沾满泥灰,嘴唇干裂得像久旱的土地,但睫毛颤了颤。 何亚胜心里咯噔一下,伸手探向她的颈动脉。 指尖传来微弱的搏动,像暴雨前远处的雷声,轻得几乎抓不住。 “活人!这是活人!”他扯着嗓子喊,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撞出回声,惊得墙角的苍蝇嗡地飞起来。 后来才知道,这姑娘叫陈翠菊,17岁,从贵州山村来东莞打工。 跟着老乡下火车时挤散了,揣着的几十块钱很快花光。 在桥洞底下躲了三天,太阳毒得像要把人烤化,她又饿又渴,眼睛一黑就栽倒了。 路人看她一动不动,身上又脏又臭,以为是哪个工地上没人管的死者,直接联系了殡仪馆。 东城医院的救护车呼啸着冲进殡仪馆时,陈翠菊的血压已经低得测不出来。 医生拿着听诊器的手都在抖,“重度脱水,电解质紊乱,再晚半小时,神仙都救不活。”护士们轮流守在病床前,用棉签沾着温水润她干裂的嘴唇,半夜里她突然抽搐,护士长直接跪在地上做胸外按压,直到天亮才松了口气,白大褂后背全湿透了。 本来想等她醒了问清家里地址,没成想陈翠菊醒来后眼神发直,只记得自己是贵州织金的,爹娘叫啥都想不起来。 医院联系了当地派出所,民警翻着厚厚的户籍本,一个村一个村地问,折腾了半个月,才在一个偏远山村找到了哭红了眼的家人。 老两口揣着医院职工捐的800块钱赶来,看到女儿躺在病床上,扑通就给医生跪下了。 出院后陈翠菊回了贵州,却总对着窗外发呆。 有天她捡起妹妹丢弃的铅笔头,在作业本背面画桥洞下的月亮,画得歪歪扭扭,却停不下来。 金华有个美术老师看到报纸上她的故事,写信说“你要是愿意,来我这儿学画画吧”。 她攥着信纸坐了两天火车到金华,第一次摸到油画颜料时,手抖得差点把调色盘摔了。 现在的陈翠菊,画里总带着光。 她的《重生》挂在浙江美术馆时,好多人站在画前掉眼泪——暗色调的桥洞下,一束光从头顶的破洞照进来,照亮了蜷缩的女孩和她手里握着的半块干硬的馒头。 2013年她成立了助学基金,资助像她当年一样的山里女孩学画画,基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何亚胜的照片,照片里的老人笑得见牙不见眼,旁边写着一行小字:“谢谢你多看的那一眼。” 那支她初学画时用了三年的铅笔,现在还放在基金展厅的玻璃柜里,笔杆被磨得发亮。 陈翠菊说每次看到它,就想起1995年那个夏天,何亚胜掀开白布的瞬间,阳光透过车间高窗斜斜照进来,落在她脸上,暖得像妈妈的手。 她用这支笔画过绝望,画过重生,现在画得最多的,是山里女孩握着画笔的样子——那是她想送给世界的,关于希望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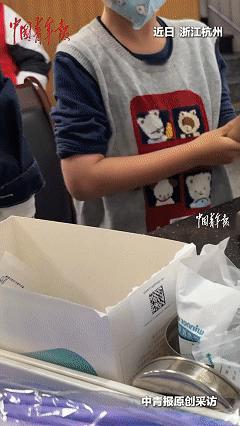







用户10xxx10
[doge][doge][do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