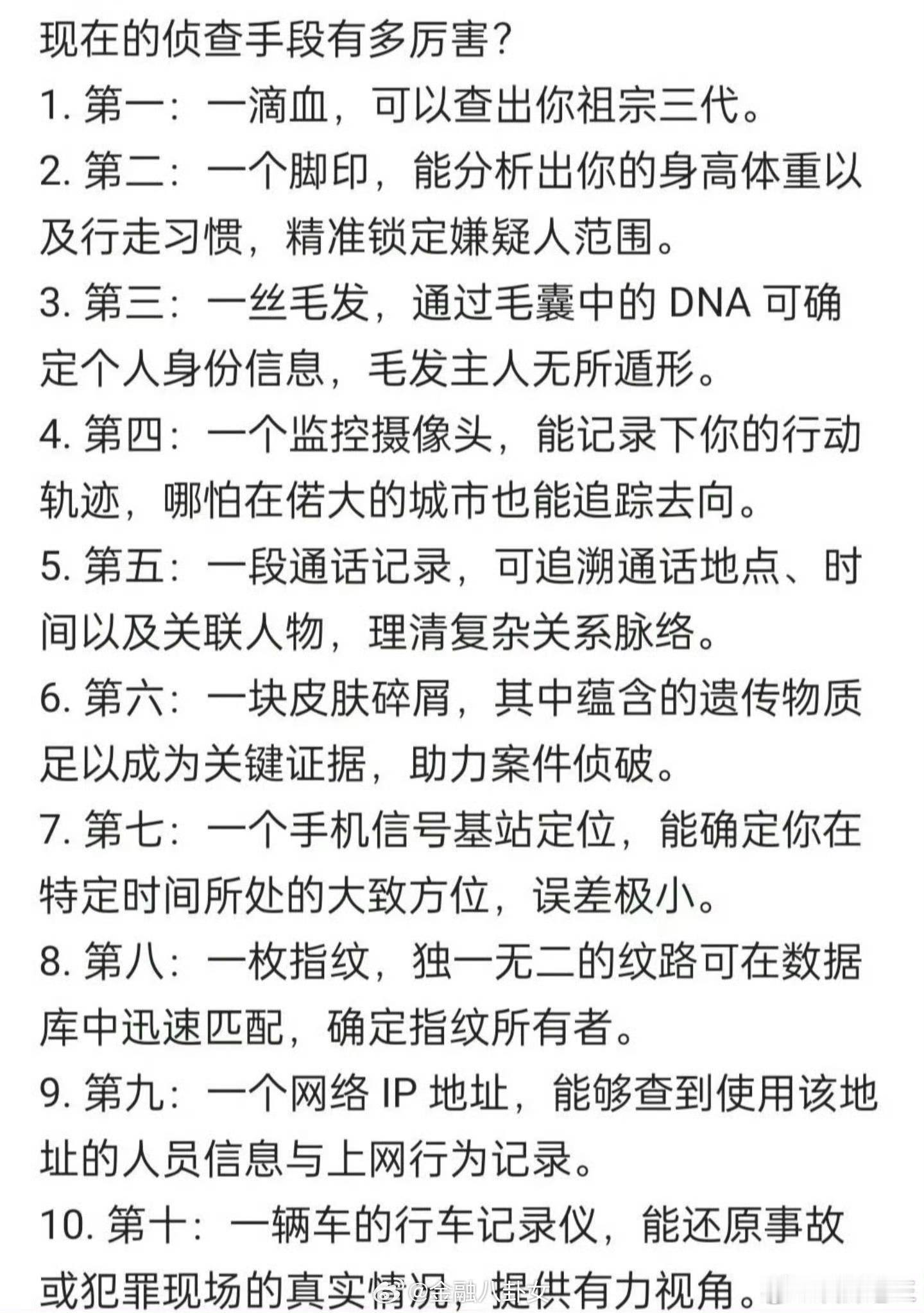今天我大伯和我二伯这对十年老死不相往来的亲兄弟终于放下以往的成见一笑免恩仇了,起因是前段时间我爷爷生病卧床不起,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才恢复,本来几兄弟要轮流照顾的,但是我大伯考虑我二伯家里条件不是很好,负担重,经常需要出去打零工维持生计,所以就索性让我二伯放心大胆的出去打工挣钱,照顾爷爷的事就由他们兄弟几人分担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我大伯和二伯的矛盾,源于十年前老家宅基地的分割。一句气话,一次算不清的旧账,让这对曾经一起光屁股下河摸鱼的亲兄弟,成了住在同一条村上却十年不打招呼的“陌生人”。逢年过节在爷爷家碰上,空气都能冻住,全靠我们这些小辈在中间硬扯些闲话。 爷爷这次病倒,像一块沉重的试金石。家庭会议上,气氛凝重。按惯例,几兄弟要轮流陪护。二伯蹲在墙角,闷头抽着廉价的烟,眉头拧成了疙瘩——他是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收入,停工陪护,家里开销立刻就得断档。他张了几次嘴,都没发出声音。 这时,一直没开口的大伯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老二,”他有十年没这么叫过了,“你家里的情况,哥知道。爸这里,有我们几兄弟呢。你该出去干活就出去干活,晚上有空了过来瞅一眼就成。” 二伯猛地抬起头,眼眶瞬间就红了。他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只是重重地“嗯”了一声,把脸别了过去。那一刻,屋里没什么感人肺腑的宣言,但横亘了十年的那块冰,就在这朴素的体谅里,“咔”一声裂了道缝。 第二天一早,二伯天没亮就去了工地。但收工后,他没回家,骑着那辆旧摩托车直接来了医院。手里拎着一袋大伯最爱吃的酥饼,衣服上还沾着灰。他没多话,接过毛巾就给爷爷擦身,动作有些笨拙,却很仔细。大伯在一旁看着,默默递过一盆热水。 爷爷还不能说话,但看看这个儿子,又看看那个儿子,眼睛里闪着浑浊的光。或许,这场病痛的苦涩中,终于渗进了一丝迟来的甜。你看,岁月和苦难有时很残酷,但它也能把那些被怨气蒙住的本心,打磨出来。亲情这东西,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