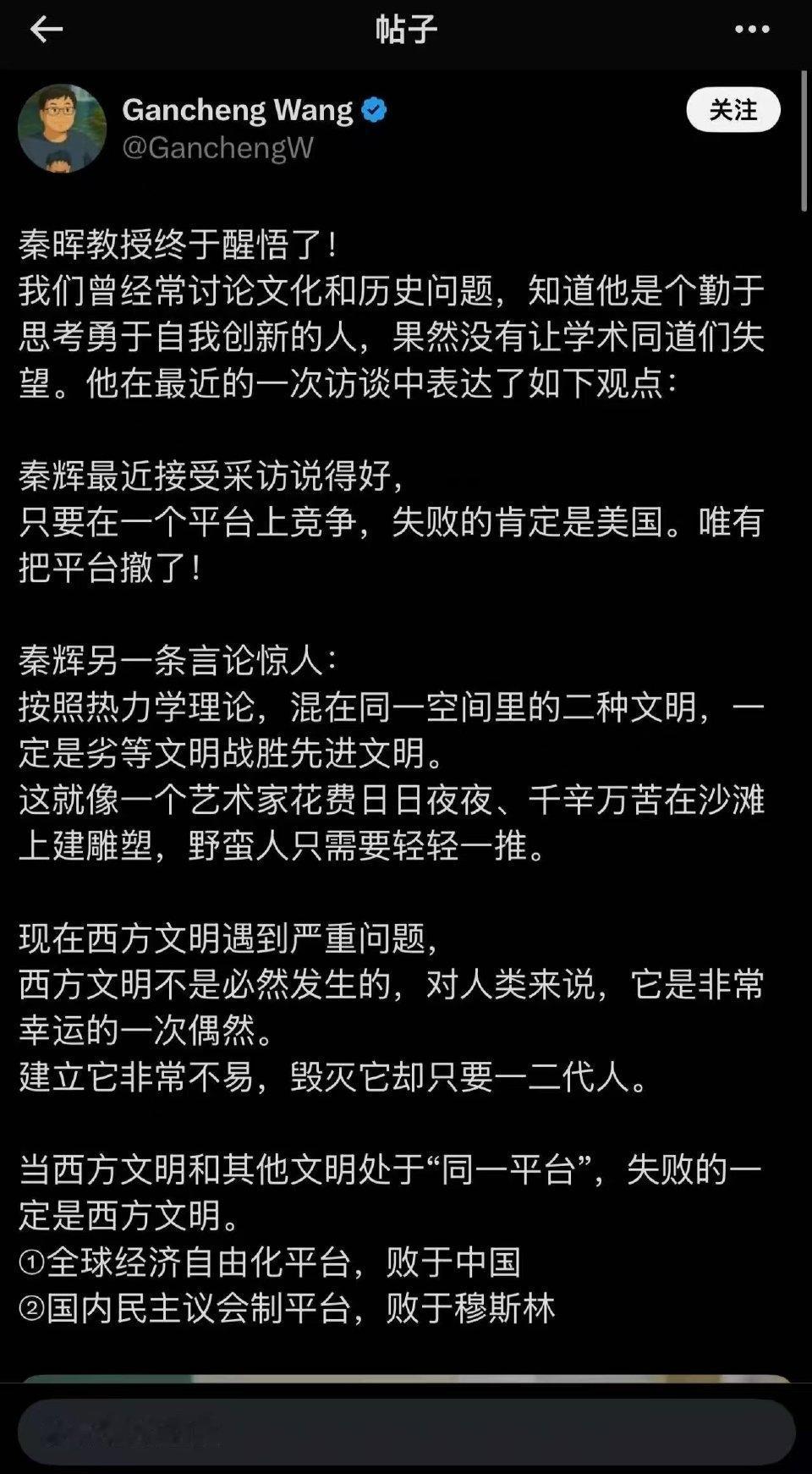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战时华夏大地,医生们直面残酷现实:在恶劣的医疗条件下,伤口一旦感染,往往就如同被下达了死亡通牒,生还希望渺茫。即便如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亦难逃厄运。他不过是手指意外划破,却因感染致使病情急转直下,最终溘然长逝。 如此结局,着实令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那个年代,一个小伤口就能轻易夺走人的性命。彼时,西方国家将救命的青霉素紧紧攥于手中,视其为最高军事机密,层层设防、严密封锁,如守财奴般吝啬,哪怕一滴也绝不让其流入中国。 汤飞凡在昆明见到李约瑟时,这位英国学者满脸怀疑。中央防疫处条件之窘迫令人咋舌,连自来水都难觅踪迹,仪器全靠东拼西凑。这般捉襟见肘的境况,竟妄图制造青霉素,谈何容易?国外同行嘲笑这是"手工作坊里的白日梦"。 汤飞凡自哈佛归来,绝非是为了在困难面前俯首。他怀揣着壮志与豪情,定要在前行之路上披荆斩棘,而非向艰难困苦轻易妥协。他心中暗自较着劲,忿忿不平:凭何外国人能够达成之事,中国人就难以成就?这股心气,在他胸膛中熊熊燃烧。 青霉素研发,菌种堪称关键所在。然而,西方对此秘而不宣,将这一核心资源捂得密不透风,使外界难窥其详。汤飞凡携魏曦、朱既明等一众青年才俊,投身一场看似荒诞不经的“寻霉大战”。他们无畏未知,毅然踏上这段充满挑战与奇幻的探索之旅。发霉的馒头、烂掉的水果、旧衣服的褶皱,只要长出绿毛白毛,都成了他们的宝贝。 技工卢锦汉那双相伴多年的皮鞋,许是遭了潮气侵袭,竟生出了一层浓密绿毛。岁月在鞋上留下痕迹,潮湿更是让它染上这般别样“景致”。搞大扫除时,别人眼里该扔的破鞋,在这群科研人员看来却可能是救命的希望。 他们谨小慎微地将那团毛茸茸之物轻轻刮下,动作极为细致,似怕惊扰分毫。而后,带着些许期许,将其送往培养之处。前前后后收集了四十多株霉菌,大多不堪用,就这双旧皮鞋上的菌株,检验下来竟然是高产品种。谁能想到,后来救活无数人的药,最初的菌种来自一只发霉的破鞋? 菌种有了,怎么把它变成药?这才是真正的难题。因无发酵罐,他们将浴缸、玻璃瓶,乃至医院废弃便盆仔细洗净、严格消毒,化其为培养容器,于困境中寻得解决之道。战时中国难以获取西方用作培养基的玉米浆,汤飞凡带领众人开展试验。他率众对豆类、麦麸、棉籽饼逐一测试,最终发现棉籽饼酶化物不仅效果更佳,还降低了成本。 昆明是日军轰炸的重点,空袭警报一响,这群人第一反应不是自己躲。而是赶紧抱起正在培养的瓶瓶罐罐往防空洞跑,生怕几星期的心血毁于一旦。实验室电力供应极不稳定,致使试验常常被迫中断。 这不仅影响了研究进度,也为科研工作带来诸多阻碍,亟待解决电力问题以保障试验顺利开展。汤飞凡毅然决然将家迁至防疫处,饿时以干粮果腹,困来便伏于桌小憩。纵然双眼布满血丝,尽显疲态,他仍坚韧不拔,不肯停下手中的工作。 李约瑟为这份锲而不舍的坚持所动容,旋即伸出援手,凭借自身之力,从国际援华机构处为其争取到了部分资助。但那点钱只够买最基本的玻璃器皿和化学试剂,大部分工作还得靠人力。没有无菌空气设备,就手动搅拌;实验室不够,就把废弃房间打扫出来,日夜连轴转。失败了就总结经验重来,遇到难题就聚在一起翻书查资料。 1944年秋,于昆明西山脚下那间简陋的实验室中,历经无数艰辛,中国第一批自制青霉素终于呱呱坠地,这一成果,开启了我国青霉素自主制造的新纪元。五小瓶,每瓶5000单位,按今天标准看剂量很少,但这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救命药。 为了验证药效,他们找到几位已经被判"无望"的败血症伤员。注射后,高烧慢慢退了,炎症得到控制,那些本该死去的人竟然活了下来。喜讯如疾风般传至前线,那消息似璀璨烟火般在战士们心间炸开。刹那间,他们眼中迸射激动光芒,情不自禁地振臂欢呼,声音冲破硝烟,直抵云霄。 产量极低,黑市上一支青霉素价比黄金。汤飞凡立下严苛规矩:此药务必优先供应前线抗日将士,以助保家卫国。他铁面无私,严令禁止任何人借此药谋取私利,尽显大义与担当。他内心明镜似的,清楚这绝非谋取财利的手段,而是关乎性命的珍贵之物,容不得丝毫亵渎与妄用,必须善加对待。在他坚持下,这批珍贵的药被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汤飞凡潜心科研,不断精进工艺。他将产量从5000单位显著提升至2万单位,还成功摸索出结晶储存技术,一举冲破西方长期的技术垄断,为行业发展立下卓越功勋。后来他在沙眼病原体研究上取得世界级成果,为了验证致病性,甚至把病毒滴进自己眼睛,顶着红肿疼痛观察四十天。这位被称为"东方巴斯德"的科学家,一生都在用知识和肩膀扛起救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