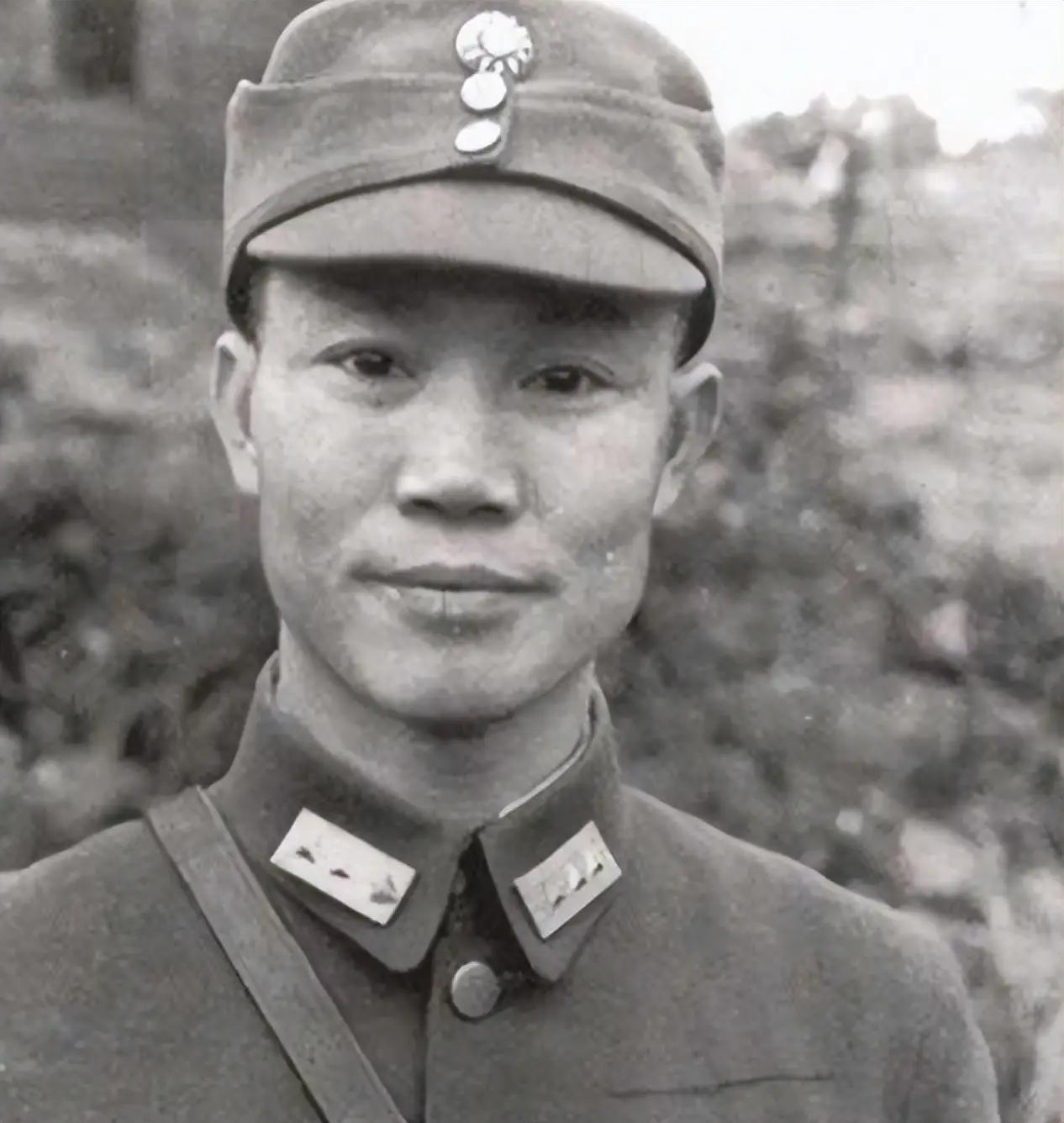吴石牺牲后,陈诚冒死护遗孤:化名"陈明德"助子女求学。 这事儿放今天,说出来都跟编故事似的,国民党里的大人物,陈诚,官不小,什么“行政院长”、“副总统”都干过,可当时人人都在抓中共特务,他倒好,顶着天大的风险,把中共烈士吴石的孩子接过来养,还给改了姓,掏钱又出力,一养就是十几年,吴石这人,1950年就被枪决了,是当时潜伏者里军衔最高的,身份一露,整个台湾都在抓他家属,谁敢沾边,那真是脑袋不想要了。 谁能想到,这种时候伸手的,不是什么普通人,就是陈诚,他和吴石是老同学,保定军校那会儿就在一块儿,后来在陆军大学又是同事,这交情,十几年下来,谁家什么情况,谁在哪个圈子,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根本不是简单的敌我对立,老同学之间有自己的规矩,吴石搞“秘密工作”,陈诚心里清楚得很,就是一直没捅破那层纸,等真出了事,陈诚直接派人去接孩子,自己不方便露面,就递了个条子,“明德兄托我照拂”,给孩子换个姓,算是拉进了自己的保护圈,身份全给换了。 那会儿台湾刚进入“战时状态”,吴石的案子闹得满城风雨,陈诚知道这事风险多大,可他一点没含糊,做事也不是随便给点钱,找个地方让孩子躲起来就算了,他是真在给孩子安排后路,托人找了教会学校,对外就说是“远亲”,学费按月给,校服都给做新的,孩子发烧了还有人专门送雪梨汤。 连校长都只知道这是“陈家的远房亲戚”,让多关照点,事情办得滴水不漏,这种体面,是那个时代的人才懂的,孩子们长大了才知道,以前在学校看的《资治通鉴》,背的那些诗,都是陈诚书房里的藏书,书上没名字,就夹个纸条,“莫负光阴”。 大年三十的腊肠,过年的新鞋,家里人不敢上门送,他就让副官带过去,话也简单,“这是应该的”,后来孩子考上台大,他送了张信纸,上面就一句,“做人要像竹子——根扎得深,腰板才硬”,这是一个军人,给烈士后代的一份成年礼,没有大道理,全是托付。 他救的不光是孩子,是一大家子的命,吴石的遗孀王碧奎,带着孩子到处躲,顶着“吴石家属”的帽子,在台北连米都买不到,房子也租不着,陈诚就一封信,把所有事都安排妥了,让他们从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活了过来,王碧奎念了他一辈子,后来回到大陆,那封信还带在身边,晚年一直放在床头,她说“他救的不止是两个娃,是我们一家人的命”。 军统恨不得马上除掉的“匪谍家属”,就这么在台北安稳读书长大,靠的不是什么“宽大处理”,是有人真拿自己的前途和人脉在背后顶着,这不是人情,是救命的恩,白色恐怖那会儿,这事谁碰谁死,陈诚敢这么干,就是真把对方当同袍,不是敌人,部队里出来的人,有自己的道义,有点古风。 他办这事,不谈政治,只论本分,吴石是共产党,陈诚心里有数,可他在任何公开场合和私人信件里,一个字都没提过,也从不对孩子说“你爹是干嘛的”,就告诉他们“要好好读书”“做人要正直”,他知道提那些只会害了孩子,能做的就是默默扛着,不求回报。 1968年陈诚去世,王碧奎带着孩子去吊唁,在灵堂前哭得不行,那不是哭一个大官,是哭一个撑了他们十几年的恩人,陈诚自己的孩子后来写回忆录说,“父亲总讲,当年做的那点事不算什么,换了谁都会帮”,其实哪是那么回事,换个人,连“陈明德”这个名字都不敢给孩子起。 什么叫情义,就是做了也不说,说了也不解释,这事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没声张,没给自己挂个“高风亮节”的牌子,也没到处喊“我养了烈士的后人”,连孩子们自己都不知道救他们的是谁,都是后来靠着书信和回忆才拼凑出真相,陈诚没解释过,他觉得这是他该做的,遗嘱里也没告诉子女自己救过谁,跟现在有点事就恨不得全世界知道的人比,完全是两个境界,这才是“士”的风骨,我做了,不图你记着,你们好好活着就行。 再回头看吴石和陈诚,真是历史的另一种写法,有人为了信仰去死,有人为了情义去活,有人牺牲得轰轰烈烈,是光荣,有人活着守着沉默,是担当。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能撑起人间体面和温度的,往往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那句“我认识他,我不能不管他”,这点最朴素的人情味,历史记住了吴石,也应该记住陈诚,因为他让两个孩子没有活成惊弓之鸟,什么叫大人物,不是官有多大,讲话多响,照片挂多高,是别人最害怕的时候,你敢站出来替人挡一下,有时候,一碗粥,一封信,一句“我来照拂”,比军功章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