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提出,这味药善于消磨瓦石铜铁之物,化坚散结之力极强!
此方子出自清代名医张锡纯,名曰“鸡胵汤”,是他用来治疗气郁成臌胀的代表方之一。
《说文解字・肉部》中对 “胵” 的记载为:“胵,鸟胃也。从肉,只声。” “胵” 是形声字,左边的 “肉”(“月” 字旁的变形)表示与身体、器官相关,为形旁;右边的 “只” 表示读音,为声旁。明确指出其本义是 “鸟胃”,即鸟类消化器官的一部分,对应现代所说的 “鸟嗉子” 或 “鸟胃”。在后续使用中,“胵” 的含义有所扩展,可泛指动物的内脏,不再局限于鸟类。
张锡纯认为,臌胀的根源在于脾胃失运、气机不畅。他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提到,《内经》早有“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之论。脾与胃相为表里,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若脾失健运,津液不布、气化失司,水湿停聚、气滞不行,就会导致腹部臌胀。因此,他治此病不单纯攻邪,而是以“理脾胃、调气化”为核心思路。
方中首用鸡内金,正是张锡纯独到之处。
鸡内金乃鸡之脾胃中膜,善于消磨瓦石铜铁之物,化坚散结之力极强。张锡纯提出,这味药能“直入脾中”,帮助脾胃化解血管中因瘀滞而成的丝块瘀结,这是草木药所不及的。他借此阐述:西医所谓“脾体中虚,血流不畅”,实与中医“脾失运化”相通。用鸡内金化瘀滞、行气化,既顺中医理气化湿之旨,又能解释现代病理变化,可谓中西互证。
张锡纯在方中又加白术,以健脾益气、扶助中阳。白术是脾胃虚弱的要药,能增强鸡内金的化瘀力,使运化之机更旺。
张锡纯认为,“补者须兼以化,化者必佐以补”,只有攻补兼施,才能使脾气振、湿浊化、臌胀消。鸡内金与白术相配,一化一补,一攻一守,正体现出他平衡中求治的思路。
此外,方中柴胡与陈皮的组合,也是张锡纯的精妙之笔。柴胡疏肝解郁、升清理气;陈皮理气化痰、调中和胃。张锡纯指出,“气郁则脾滞,脾滞则湿聚”,若气机不通,补化皆难施展。
柴胡与陈皮,一升一降,使气机条达、脾胃得运,是理气调中的关键。张锡纯特别强调“理气为治臌之要”,此二药即寓此意。
再加上白芍与生姜,使方更为周全。张锡纯认为,气臌虽主于气郁,但多兼水湿。
白芍能养血柔肝、调气行水;生姜温中散寒、调和营卫。两者合用,既能行气化湿,又可和营护胃,使全身气化流畅。张锡纯称此方“治气郁兼湿胀,攻补兼施”,全方升降并调,气血互通,堪称理脾调气之妙剂。
张锡纯还留下了一则亲历医案:
有一位六旬老者,腹胀如鼓,饮食不进,脉象沉滞。服鸡胵汤数剂,初效不显,他判断病情兼有宿滞,遂加黑丑,炒研细末,煎汤送服,仅两剂便腹胀渐消,再去黑丑续服数剂而痊愈。若病人小便短赤、灼热者,他会酌加滑石清热利湿。这一医案充分体现出他灵活辨证、以理化病的思路。
不过,张锡纯亦提醒:鸡内金虽善消积滞,但《本草》记载其“能缩小便”,若病人本就有水气不化、小便不利之证,须慎用。因此方中配入白芍,正是为防止鸡内金太燥,以其行水之性弥补短处。张锡纯并强调,辨气臌与水臌有法:气臌者,按之即起,小便多正常;水臌者,按之陷而不起,小便多不利。气臌宜理气化湿,水臌宜利水渗湿,辨证准确,则药到病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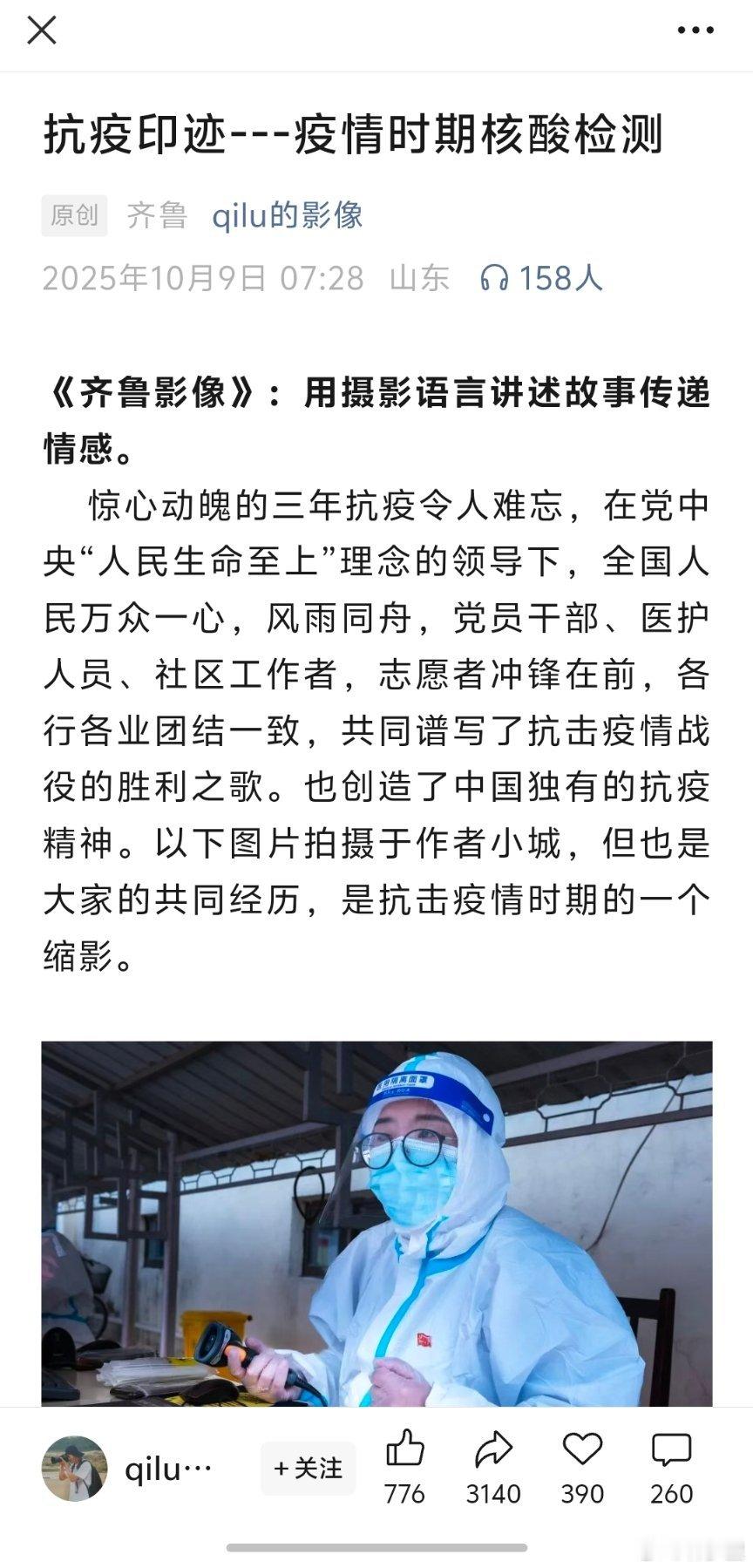
![瑜伽小姐姐,如果没这纹身就完美了![赞]](http://image.uczzd.cn/4048414739028849190.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