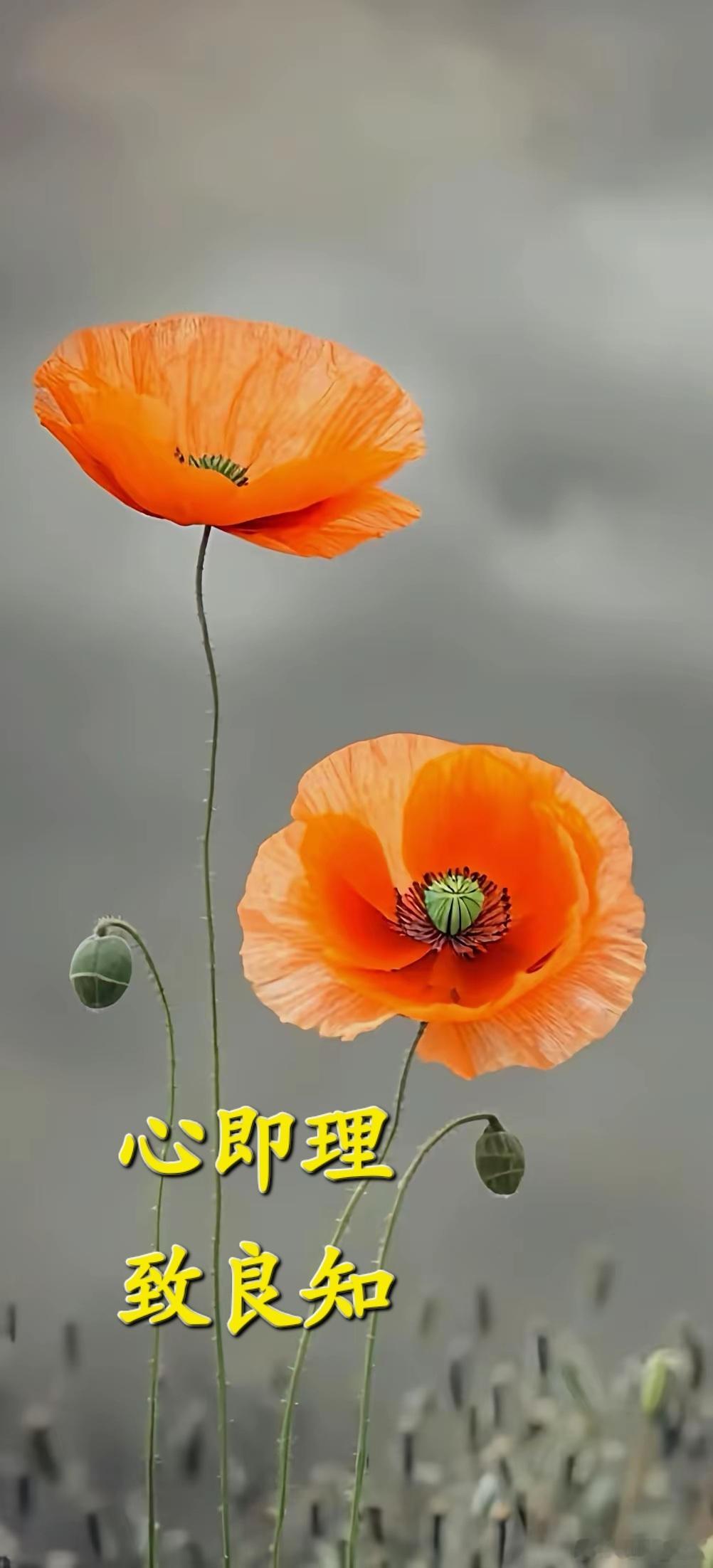刘渡舟教授认为只要抓住主证,用对方药,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刘渡舟教授看来,《伤寒论》的方证辨证体系之所以历久弥新,关键就在于一个“抓主证”。他指出,《伤寒论》中每个方剂都有一个明确的主证,这个主证是张仲景在大量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的、最能体现该方治疗特征的症状组合。主证不仅是辨证的核心,更是诊断和用方的依据。只有先抓住主证,才能找到辨证的重点。换句话说,主证就像疾病的“主脉”,是病理变化最集中的外在表现,抓住它,就等于抓住了病机的关键。刘老认为,抓主证的方法最大的特点在于简明实用。它不需要一开始就复杂地分析病因、病位、病势,而是通过主要脉症来直接确定方药。病机的理解,其实都隐含在主证的辨析中。主证与方剂密切相连,辨出主证,也就找到了合适的方。正因如此,抓主证的方法成为历代医家最常用、最实用的辨证施治手段之一。印会河先生曾用这一方法行医数十年,积累了大量经验并编著成书,可见此法在临床中确实大有成效。从更深的角度看,抓主证并非治标,而正是治本。疾病的“本”,就是病理本质的核心变化。中医认识疾病的方式,往往不是直接解剖或化验,而是通过投方施治,再根据疗效反推病机。例如真武汤能治阳虚水泛的病症,患者服后病愈,说明病机确实是阳虚水泛。历代医家正是通过这样的临证反复验证,逐步总结出各病的主要病理特征,也就是主证。像小柴胡汤的“七症”、麻黄汤的“八症”,这些经典主证就是古人治病求本的智慧结晶。只要抓住这样的主证,用对方药,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抓主证并不是僵化地一方一证,而是要了解“一方多证”的灵活性。刘老强调,《伤寒论》中的方证体系既要懂得一方一证,更要明白一方多证。例如葛根汤,《伤寒论》中有“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也有“太阳与阳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同样是葛根汤,但主证不同,病机亦有差异。五苓散在太阳病篇中治膀胱气化不利之水气内停,在霍乱病篇又治脾胃寒湿、上吐下泻之证。吴茱萸汤在阳明、少阴、厥阴三篇中均出现,主治虽同,脉症组合却各有特点。这些都说明,主证虽为核心,但应用要灵活,应在理解病机一致的基础上因证施治。抓主证的方法还强调“知常达变”。方证有常态,也有变证。刘老举大青龙汤为例,典型主证是“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痛、不汗出而烦躁”,这是常;而另一条说“脉浮缓、身不痛但重、乍有轻时”,这就是变。虽然脉象和身痛变化了,但只要“无少阴证”,而“不汗出烦躁”的主证依然存在,就仍可用大青龙汤。也就是说,只要病机未变,方证即可通用。医生临证时,必须明白这一点,不可拘泥于教条,而要从变化中把握不变的核心。为了真正抓对主证,刘老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明理,熟悉《伤寒论》的基本病理与方证理论;二是要熟读原文,反复诵习,把各方主证记熟记牢;三是要有程序。诊察时,要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收集与辨证相关的主要信息,再与记忆中的主证系统对照分析,看是否吻合。判断过程中要多方考虑、灵活思维,不可死板。一旦发现脉症符合某一主证,就应果断下方。刘老还总结了抓主证的几个临床要点。首先,“不必悉具”。经典中所载的主证是最典型的组合,但临床上往往不会全部出现,只要具备其中最关键的症状即可下方。张仲景在书中说“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这正是抓主证的重要原则。其次,要“删繁就简”,面对复杂的症状,要找出最能代表病机的几个关键点。刘老形象地比喻为“千军万马中取上将之首”。第三,要“辨别疑似”,因为有些主证彼此相似,要仔细分辨,否则容易误诊。第四,要“灵活变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伤寒论》中的很多条文都体现了这种思路,如“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就是根据病情轻重、缓急而调整先后;少阳并阳明时,则根据舌苔、大便情况选择小柴胡汤或大柴胡汤,充分体现了灵活性。从整体来看,抓主证的方法是辨证施治与专病专方的结合。它既能体现中医“治病求本”的原则,又能在纷繁复杂的临床现象中抓住核心。正如刘老所说,抓住主证,就像纲举目张、抽丝剥茧,再复杂的病情也能理出头绪。掌握了这个方法,中医辨证就不再繁琐,而变得清晰、有力、实用。这种由主证入手、由方悟机的思路,不仅是《伤寒论》的精髓,更是中医辨证论治永恒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