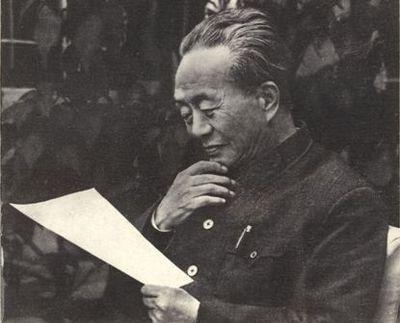1996年,艾青病逝,终年86岁。安葬那天,送别的人群中,高瑛穿着朴素,没说一句话。她安静地看着棺木落入墓穴。几十年陪伴,从青年到老年,她未曾离开一步。 没人记得她是怎样被他看上的——那是五十年代,北京作协后院的工间操时间。她当时22岁,刚调来不久,有两个孩子。每天早上,她总感觉有人盯着。抬头看,楼上窗口,一名中年男子站着,目光没挪开过。 她以为是错觉,换了地方做操,那个目光还是跟着动。她问同事,那人是谁?得到的答复让她一怔:艾青,写诗的。 这个名字她再熟悉不过。七年前,她在哈尔滨念师范,读到他的《卖艺者》,震动很久。那时她无法想象,有朝一日,这个写出沉痛诗句的人会站在窗口,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几天后,艾青找机会接近她,约她一起去看电影,甚至说是带妹妹出门,其实只是想多接触几次。两人慢慢开始聊天,她没隐瞒自己已婚的身份,还说出了真实处境——结婚前被隐瞒,丈夫在乡下有原配和孩子,想离婚却迟迟无法解决。 艾青听完,在后院抽了很久的烟。第二天,他递给她一张纸条:春明食品店,上午九点,来见我。 她犹豫了一整夜。一个著名诗人,年纪大她23岁,又刚打完五年离婚官司,看起来怎么都不像是个稳妥选择。她心里防着,却还是准时出现在那家店门口。 见面那天,艾青没绕弯子。他说:“我知道你结过婚,我也有过复杂的感情。我不玩感情,我是认真的。若你家庭安稳,我绝不会打扰。”她听完没有立刻答应,只说了一句:“若有缘,就别错过。” 他们的关系迅速被前夫察觉,对方直接在单位举报,说她与艾青勾结破坏家庭。那个年代,这类风波往往牵涉严重。她被隔离审查,调岗写检查,艾青则一度失联。 为了传信,她翻出托尔斯泰的小说《家庭幸福》,在几行文字下划了红线。书通过编辑辗转交到艾青手中。他一眼读懂了暗语:“我爱他,无所畏惧。” 审查结束,她收到离婚判决,也被判劳教半年。但那一年,1956年3月27日,她和艾青登记结婚。 一年后,他们有了儿子。孩子出生不久,风波又起。有人施压让她离婚,她当场表示:为了这个家庭,自己可以退团,但不退婚。 1958年,她带着一儿一女,随艾青去黑龙江、再到新疆生活。那一走就是21年。冬天种菜,夏天养鸡,她是编辑也是家务主力,什么都得会。艾青身体不好,眼疾、疝气、慢性病不断,她帮他查资料、处理家事,一点没离开过。 1978年,艾青重返文坛。她陪他回北京,继续为他收拾稿件、安排日程。为了让他吃药,她每天亲自将药碾碎,藏进酸奶里,骗他说“今天的酸奶特别香”。 她从没抱怨过。有人说她失去了个人空间,她却写了一首诗叫《藤》,只一句话:“她爱上了谁,就和谁缠绵一生。” 多年后,艾青出国访问,每次都带回礼物。在巴黎,他把烟卖掉换钱给她买手表;在日本,他挑了双鞋,用袋子拎着上飞机,就怕压坏。 她始终记得那个站在作协窗前的男人,一眼望了下来,望了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