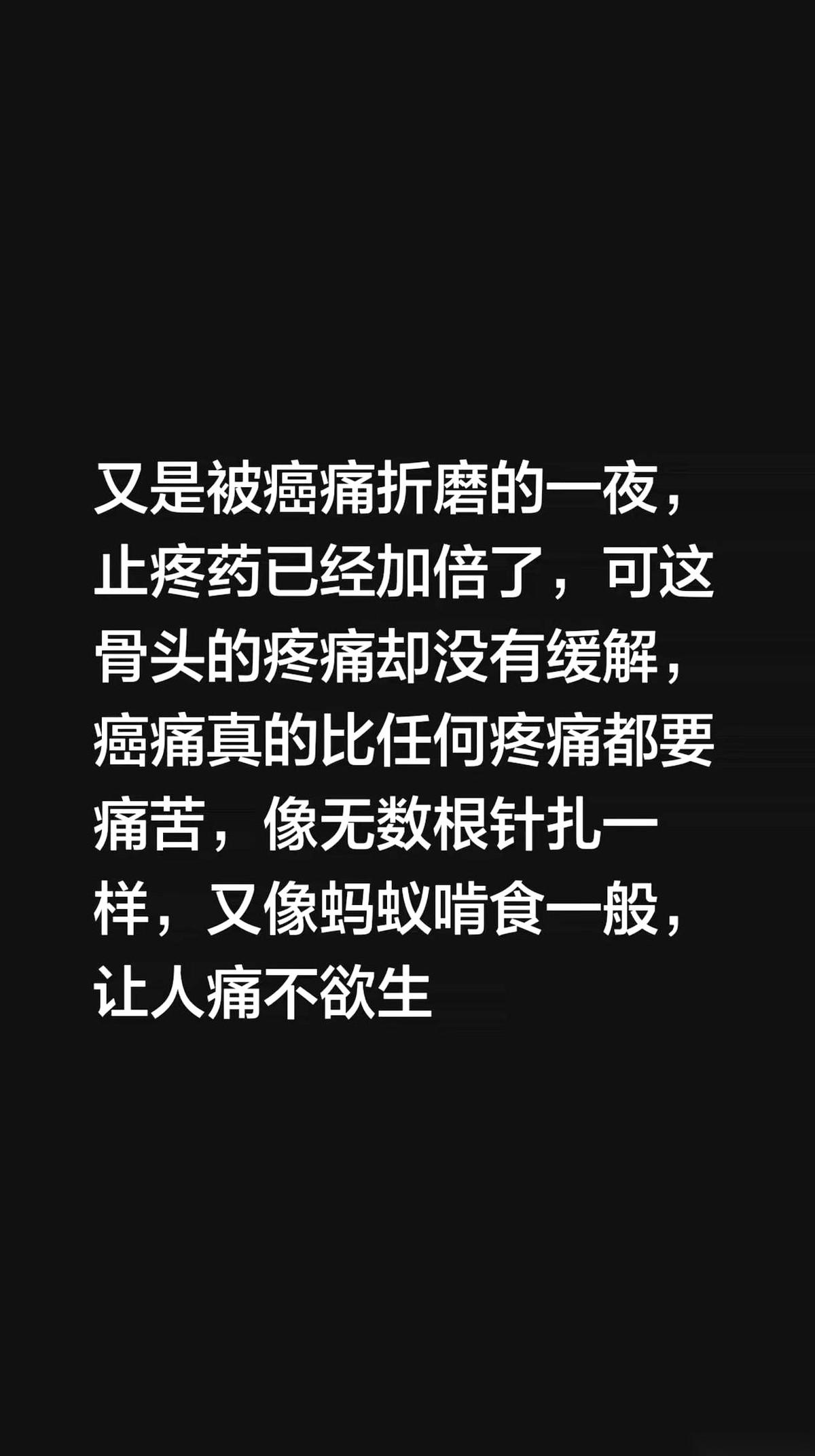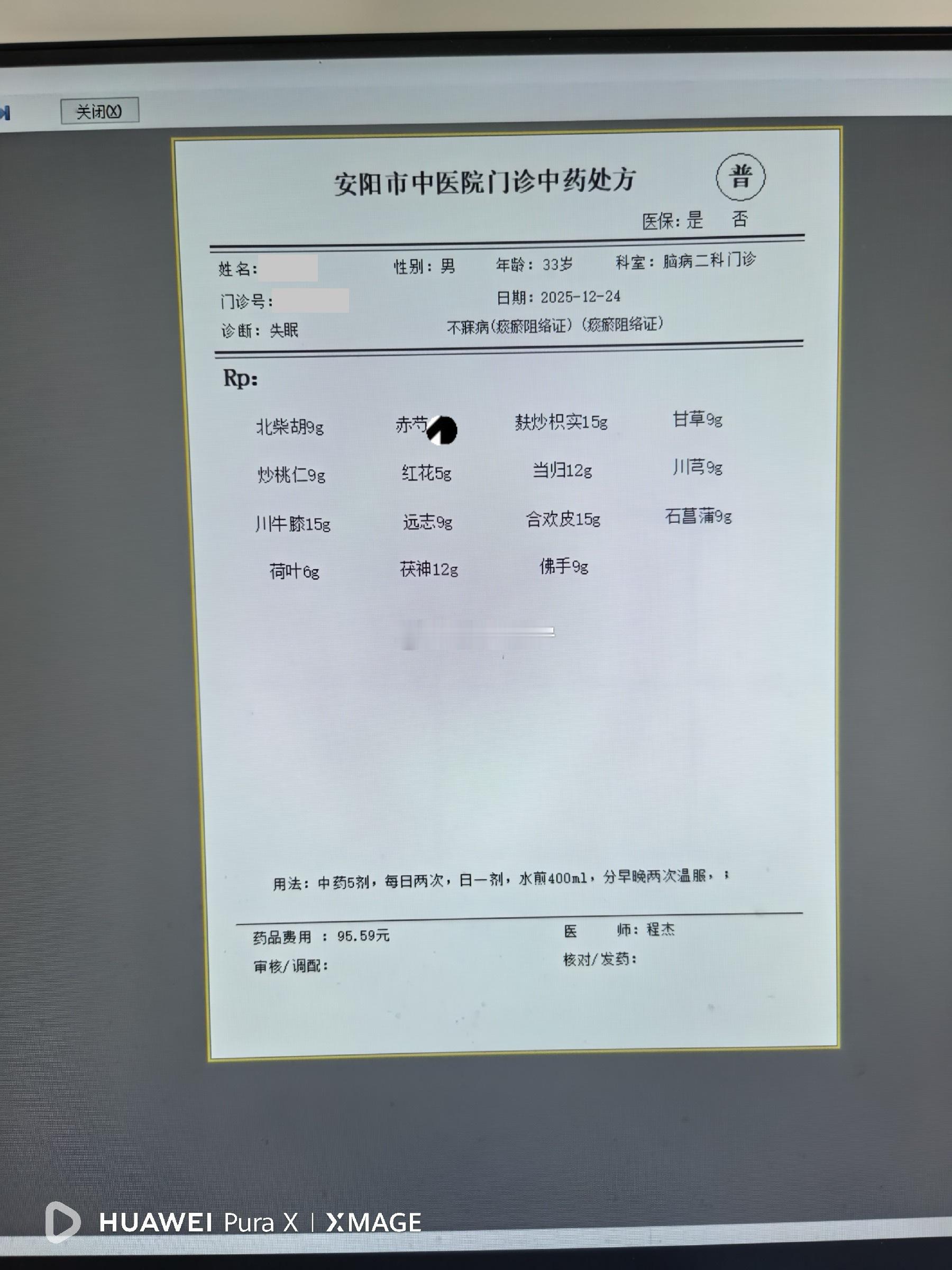止疼药的剂量,已经加了一倍。 骨头里的那股劲儿,却像要活活把我撕开。我攥着床单,手背上青筋一根根暴起,汗水把整块枕头都浸得冰凉。 医生把那张CT片子举到灯下,指着上面的阴影,嘴巴一张一合。他后面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清了,只看见“再次进展”那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一下烫在我的眼眶里。 新的治疗方案,就摆在桌上。 可之前的账单还压在抽屉底,亲戚朋友的电话,我早就没脸再打。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诊断单,还没走出医院大门,家里电话就来了。听筒那头声音发抖,说我公公也病倒了。 那一刻,我捏着手机,看着人来人往的大厅,天花板上的灯明晃晃的,我却觉得天黑透了。 老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我这哪是连夜雨,这分明是天上下刀子,还没给我留一把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