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太原村民在地头取土的时候,意外的挖到了两块4斤重的大金锭子,看四下无人,竟然直接揣进自己的口袋里,谁知,回家后却再也睡不着觉了。 二月的太原南郊,黄陵村的土路上王大柱正扛着铁锹往村东头走。 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挖两筐土修补漏风的猪圈。 春播要到了,家里那头老母猪正拱着圈门,等着下崽。 铁锹落下时,突然“铛”一声闷响,像磕在石头上。 王大柱奇怪的蹲下来扒土,指尖先碰到个冰凉的硬物,再挖开,两块马蹄形的金属块躺在土里。 这两块金锭足有四斤沉,王大柱用牙咬了咬,齿印陷进去,是真金。 他攥着金锭站起来,四处张望了,见没人赶紧收起来。 这不是普通的土块,是能换半辈子粮的宝贝。 可等他攥着金锭往家走,手心全是汗。 因为那会儿私藏文物是“现行反革命”,要蹲大牢的。 到家时,媳妇正在织毛衣,抬头看见他裤兜鼓着,张口就要骂:“你偷了谁的东西?” 王大柱赶紧掏出来:“是挖土挖到的,你看这上面的字。” 金锭底部刻着细小的楷书,“洪武二十三年”“山西布政使司造”,媳妇凑近看了,吓得手也抖。 “这是官银吧?咱要是藏了,要杀头的!” 那夜,王大柱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窗外的风刮得窗户纸哗哗响,他摸着枕头底下的金锭,一会儿想起村支书说的“文物是国家的根”,一会儿想起邻居家孩子饿肚子的模样。 50块钱能买三袋面粉,够娃吃半年,但拿了这金锭,睡觉都不踏实。 天快亮时,他终于爬起来,把金锭塞进布包:“我去村长家。” 媳妇在后面喊:“你疯了?” 他没回头:“疯的是想把这玩意儿据为己有的人。” 王大柱揣着布包找到村长,村长看了金锭,脸都白了。 “你从哪儿挖的?” “晋王陵那边。” “赶紧上报!” 当天下午,县博物馆的老专家就来了,戴着白手套捧起金锭,在放大镜下仔细观察。 “这是明代官制金锭!看铭文,是潞州府折收的秋粮赤金,抵得上五十两税银!” 专家的话让王大柱懵了,原来这不是“宝贝”,是明朝人交的“税”。 两块金锭,一块刻着“潞州洪武二十三年折收秋粮赤金五十两五钱重”,提调官吏、司吏的名字都清清楚楚。 另一块底部的字磨得模糊,但还能认出“五十两重”。 按明代的衡制,十六两一斤,这两块刚好是“五十两”的官锭。 是当年潞洲府交给朝廷的秋粮折金。 要明白这两块金锭的来历,得先说说晋王朱棡。 朱棡是朱元璋的嫡三子,眉目俊朗,却天生暴戾。 洪武十一年封晋王,封地就在太原。 他仗着是皇子,鞭挞过朱元璋的御用大厨,甚至想谋反。 洪武二十四年,太子朱标求情,才留了他一条命。 可这位残暴的晋王,却赶上了潞洲最富的时候。 晋商的驼队从这里出发,潞绸、潞铁远销全国,连税都能用黄金交。 《明太祖实录》里写着,洪武二十三年,潞洲府“以金代粮”,把原本该交的秋粮折成赤金,装在木匣里送进南京。 这两块金锭,应该就是那批税银的一部分。 或许是某个库吏疏忽,或许是战乱流失,最终埋进了晋王陵的土里,等了六百年,被王大柱挖出来。 最后,博物馆给王大柱的奖励是50块钱和一张奖状。 50块钱在当时不算少,够买一头小猪崽、三袋面粉、两匹棉布。 王大柱把奖状裱起来,挂在堂屋正中央。 村里人说“太傻”,他却笑着摇头:“公家的东西,拿了烫手。我王大柱没读过书,可懂‘不该拿的不拿’。” 如今,那两块金锭躺在山西博物馆的展柜里。 去游览的时候,还能看清“提调官吏冯瑀”的名字。 王大柱已经不在了,但他的故事还在黄陵村流传。 其实,那两块金锭从来不是“横财”。 它们是明朝的税单,是潞洲的繁华,是一个农民对“规矩”的坚守。 比黄金更重的,是“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的良心。 比文物更有价值的,是一个普通人选择“对”的勇气。 就像那两块金锭,躺了六百年,终于回到了该去的地方。 不是某个人的腰包,是国家的博物馆,是所有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或许,这就是文物最动人的地方。 它不是冷冰冰的金子,是活着的历史,是普通人的良心,是我们和祖先,最温暖的连接。 主要信源:(山西省文物局1972年档案、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登记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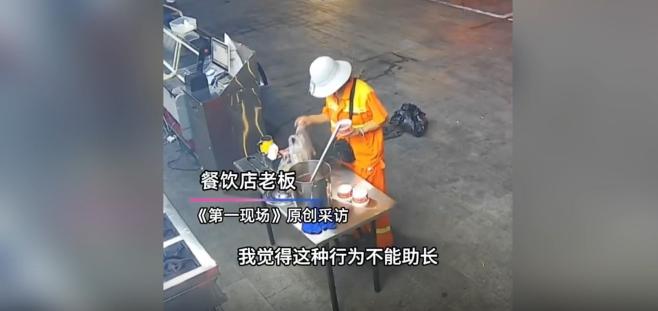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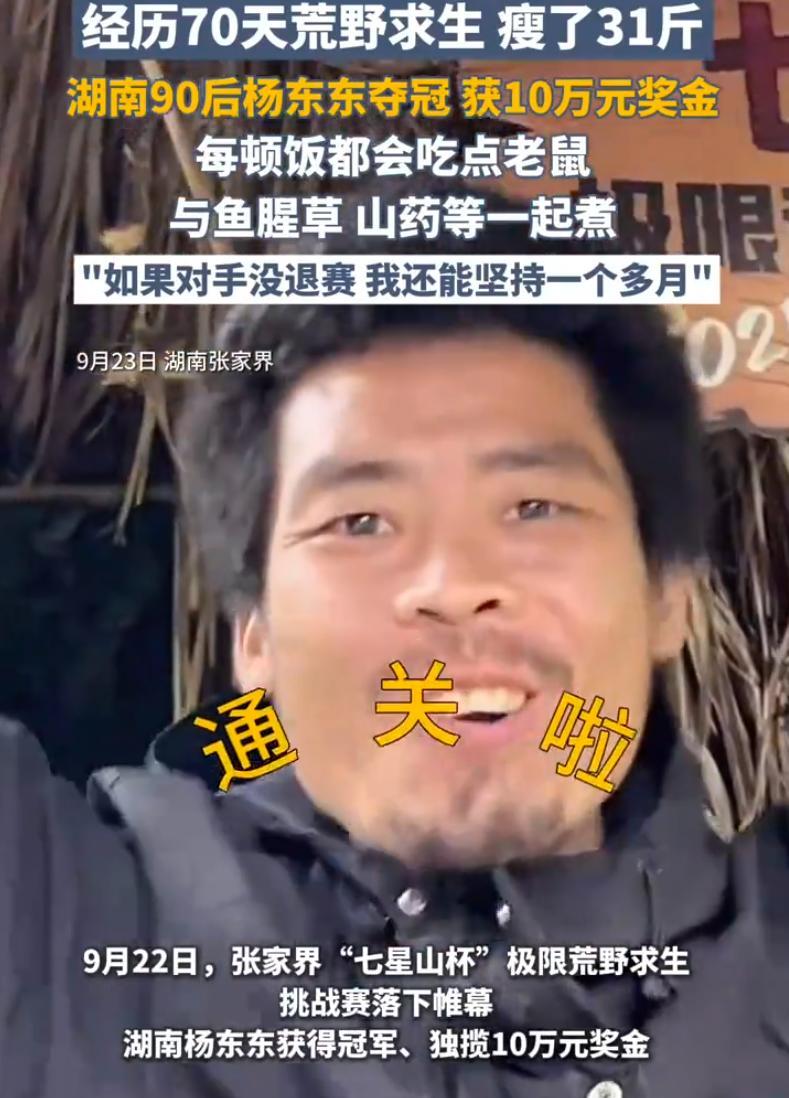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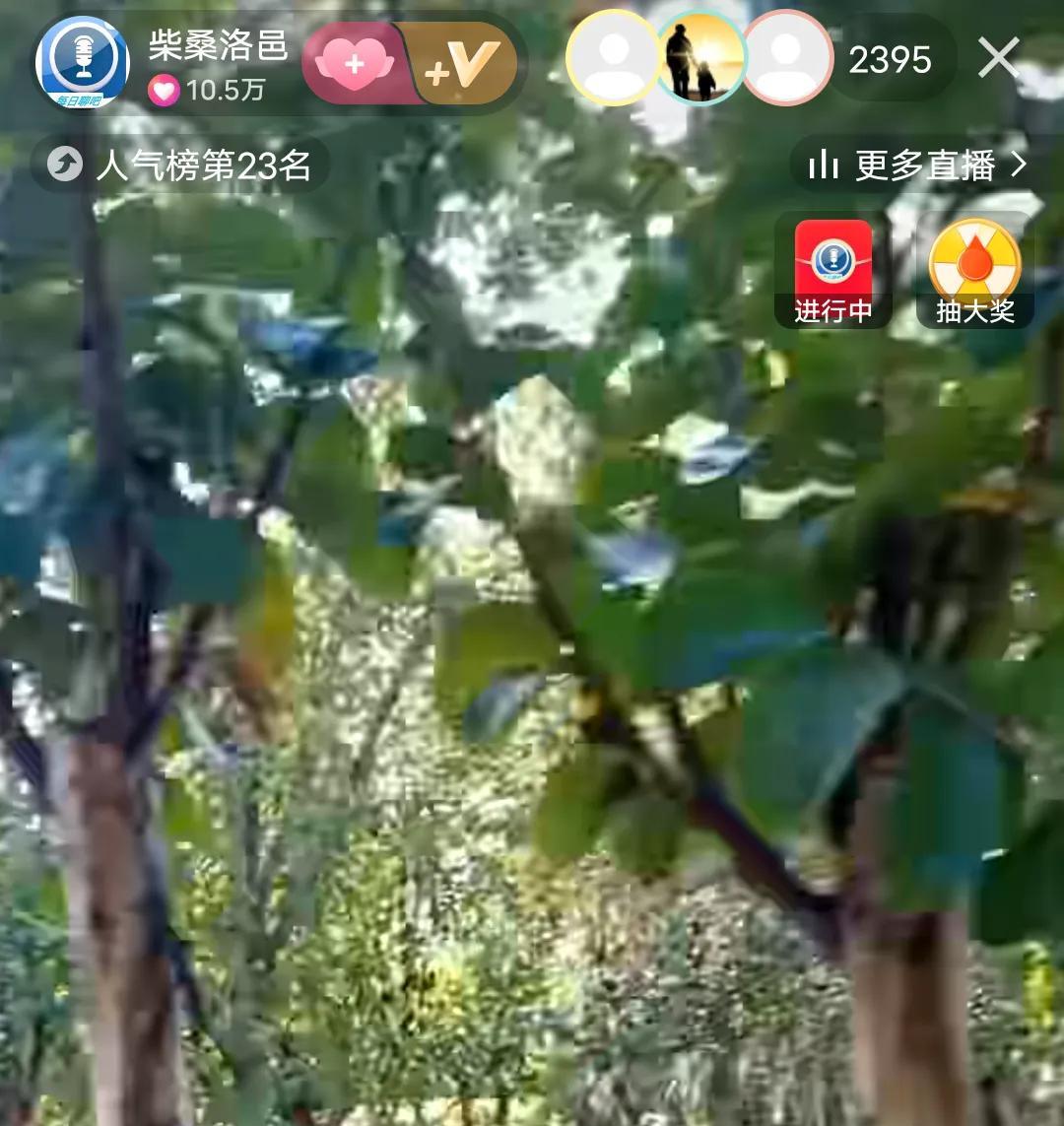

云雁
十六两一斤两块正好五十两,怎么算出来的…
湖人
文物只要不运出国,还不如保存在民间
wang
为什么很多文物外流了??????因为价值一亿元的,上交奖10块钱!!然后偷卖给外贼卖100万。。。再然后专家们花20亿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