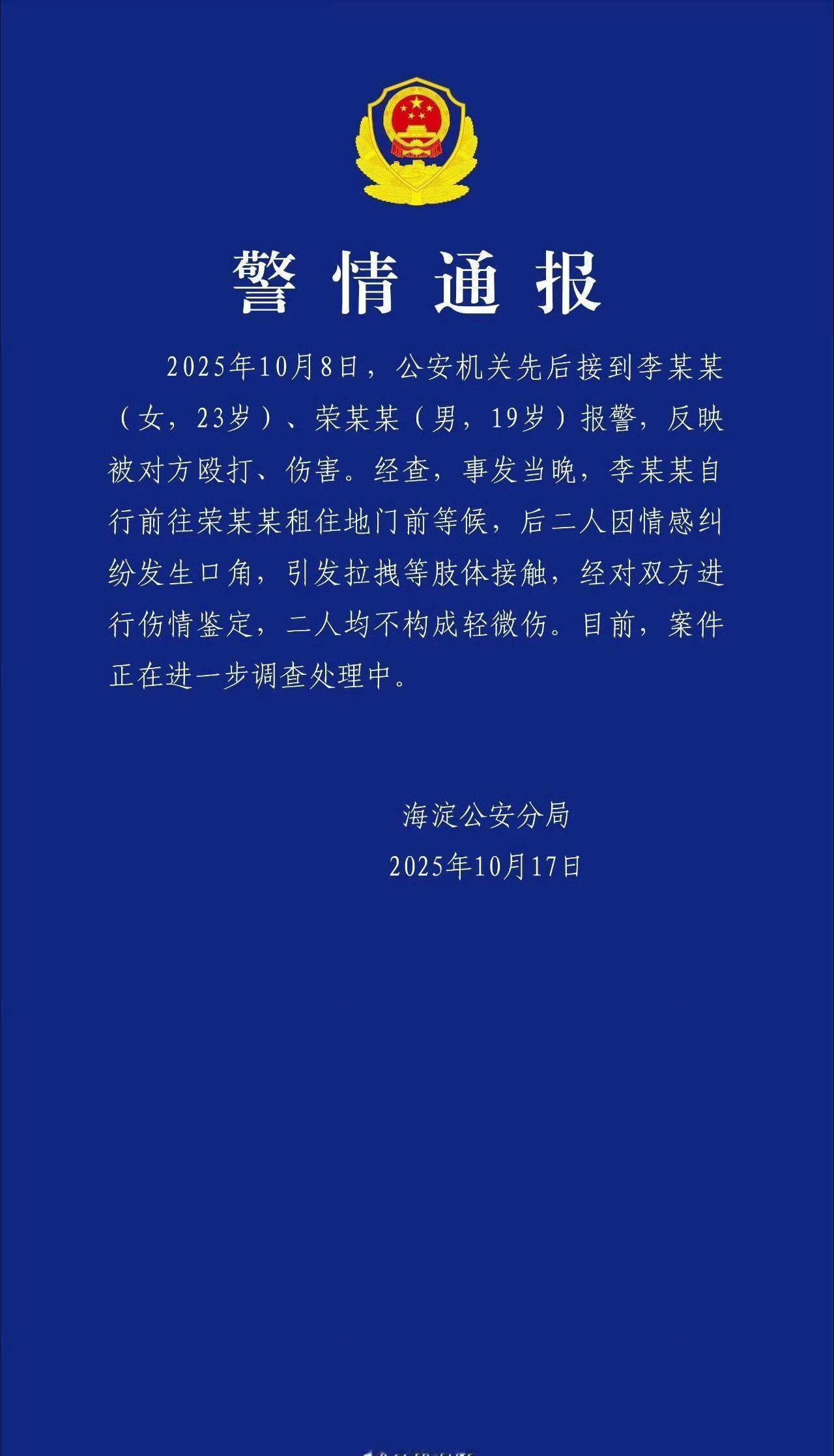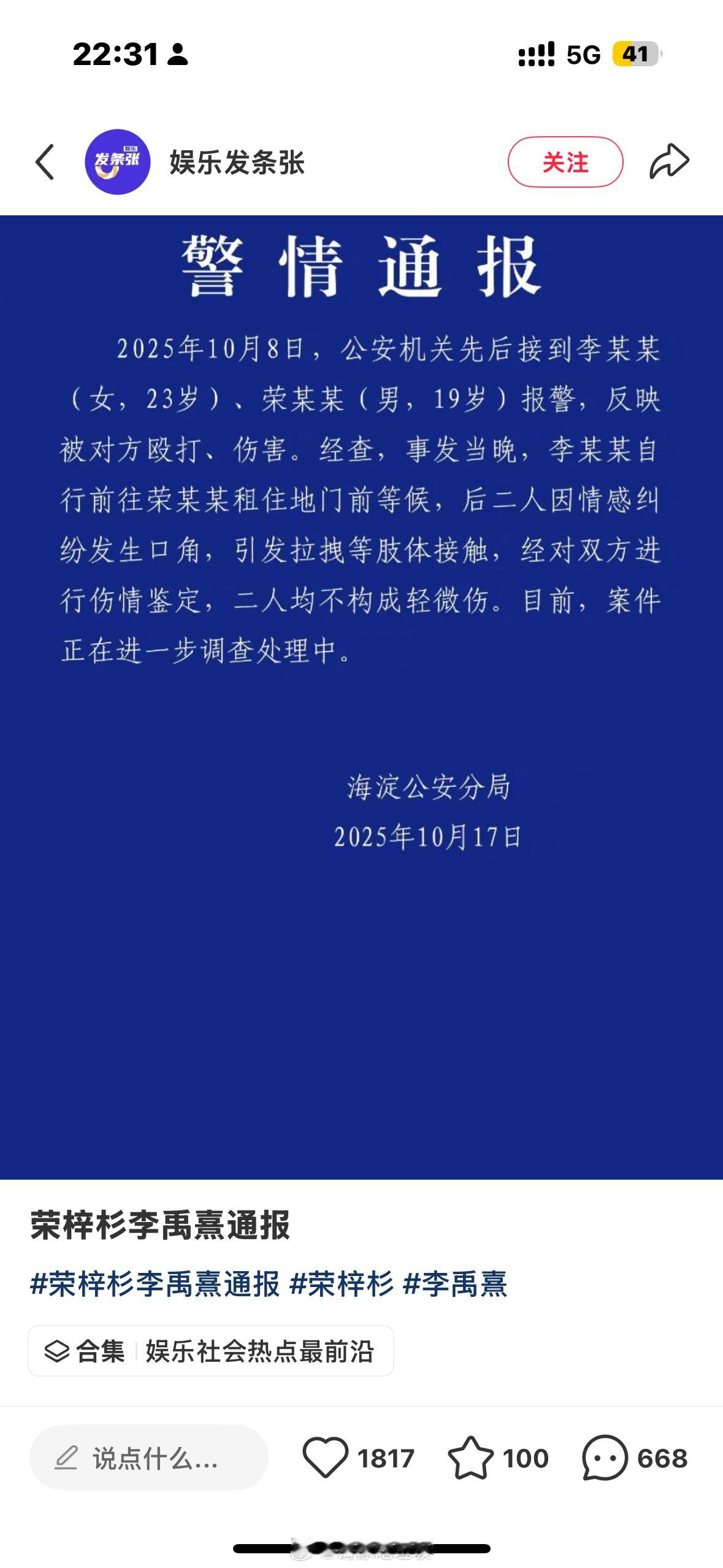1977年,由于成分不好,知青赵方奎9年都没能回城。队里得了个县邮电局招工名额,不看成分,可赵方奎却拒绝了。 这一下,把红旗大队的人都惊住了,真不夸张。谁家做饭时都得顺嘴念叨两句,连场院里晒谷子的老太太都摇头。上心的人不少,记得最清楚的是会计李有根,他打算盘的手都停了半晌,叹了口气说这小子轴。可赵方奎跟往常一样,天还没亮就去挑水,回头把破庙的窗缝堵一堵,碗柜里找出一截铅笔芯削一削。孩子们背书,他在门口听风声,看看是否又要落雪,怕孩子穿得薄。那些细碎的事儿,叠起来就成了他每天的日子,没有啥响动,却扎实。 秋收过后,白天上课,晚上他点一盏油灯,给大人开识字班,妇女多,腰里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碱水味儿。屋里没有黑板,他就用废麻袋刷成白面,钉在墙上,写大字,读报,从“粮票”“布票”讲起,一句一句抠词眼。队里有台坏收音机,他拆开拿针头焊,半夜里能鼓捣出个响儿,第二天就让孩子们围着听新闻,告诉他们外头的风换方向了。小顺子爱钻牛角尖,见算盘拨得溜,他就让孩子用火柴盒串铁丝做个小算盘。人家说他把学校当家,他也不反驳,笑一笑,继续忙。 到了冬天,一场大雪压塌了庙檐的一角,土坯掉下来,砸裂了课桌的边。没办法,他带着大孩子把桌凳挪到牛棚旁边的空棚子里,门口挂上一层塑料布挡风,脚下垫秸秆,手背被冻得开口子。晚上他把自己的棉背心拆了,缝成门帘,缝线歪歪扭扭,遮风还管用。有人说他倔,有人说他心眼大,这话传着传着,就有人悄悄把一捆柴火和半袋麦麸放在门口。娘的信也来得勤,字歪了,墨印在纸上花成一团,他摸着那纸,心里一热一凉,第二天把攒的票包起来托人往城里捎药。 雪一化,地里出青,他领着孩子在庙后挖坑,没选白杨,挑了几棵槐树,省水耐活,夏天也荫凉。孩子们把旧瓶子洗干净挂在枝头,当风铃,写上生字,一吹就响,读起书来更起劲。集上来了旧书摊,他当场挑了几本,翻背影也破了,照样抱回去糊封皮。周末他去公社口写信代笔,帮人给在外地的兵娃子写家书,挣下两张粉笔票,顺手又问问文化站的消息。文化站的年轻女干事说,扫盲要搞起来,让他帮忙统计名单,他点头,说乡亲们认字不占地儿,咱干。 又到麦黄时,暴雨把通往二队的土桥冲出个坑,孩子过不来,他就绕远,踩着淤泥挨家叩门,冲着屋里喊明天换个路口集合,别掉沟里。他背着小个子的走过稀泥,裤腿上结了厚厚一层泥壳,到了棚下才用木棍敲掉。嗓子一天到晚喊,晚上就用盐水漱漱,第二天照旧站在前面。他把邮电局的名额让出去的消息,后来才传到老陆耳朵里,老陆家里四个娃,咬着牙去报了名,年底领了薪水,给孩子添了棉袄,这事在村里也就有了个踏实的落点。 风口的事也不是没吹到他这儿。公社来了个干事,女的,脚步利索,拿着卡片册来摸底,说要登记民师情况。她翻孩子们的作文本,抬头问他怎么备课,他把那本被油手摸花了的《算术》递过去,说夜里抄的,别嫌脏。她没多说啥,回身把墙上用墨刷出的“早上读一页”照着记下,临走拍了拍他袖子,说回去给领导说说看。过了半个月,他接到通知去县里短训,回来时胸前别了个小牌,写着“民办教师”,每月能领一点点补助,他把第一笔钱换了两盏玻璃罩,晚上课堂一下子亮堂了。 再往后,电线拉到了村里,灯泡一亮,孩子们拍着手叫好,庙墙外面贴着他写的新课表,连周二的夜校也规整。有人打听他后悔不,毕竟去邮电局穿制服多体面,他笑笑说穿啥都得把扣子扣好,扣不齐也白搭。娘的病一阵好一阵,他往返两趟县城,托人买了个软枕头,怕她躺得硬,他还惦记着给她讲孩子们的笑话,让老人家能睡个稳觉。夏天的风拐过槐树,叮叮当当的风铃响,孩子们一字一句跟着读,他在门口抻了抻衣襟,心里盘算着下个学期要把地理课也带起来。若是你当年在场,你会怎么选呢?
1977年,由于成分不好,知青赵方奎9年都没能回城。队里得了个县邮电局招工名额,
成熟熊猫
2025-10-16 18:31:06
0
阅读: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