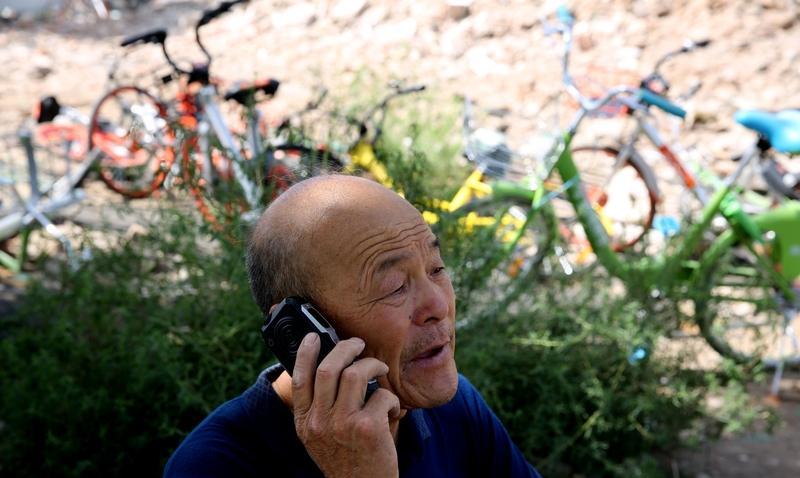老爸常说到那年中秋节生产队里抓阄分肉,老娘抓了两份,都是猪腿,当时就嚎啕大哭。 每回他这么说,我脑子里就能闻到一股热气,像从灶膛里冒出来似的,带着萝卜甜味。我是他们的大儿子,听着这些旧事长大,心里慢慢长出个笨道理:占了便宜,心里不踏实,得想着怎么把热乎劲散出去。今年临近中秋,天还闷热,我心里又开始打鼓——不是矫情,是真怕自己做得不够像话。老娘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但遇见“分东西”三个字,手上就不由自主地抠衣角。我看见她那样,就知道,又该轮到我张罗了。 前一周,镇里跟合作社、快递点合搞了个“秋礼包”,说给老人和孩子送福利,油米粉条配点排骨,寄到各家门口。我在村群里做志愿者登记,脖子上挂个工作牌,笔帽咬得都有牙印。到了那天傍晚,门口就堆了两箱礼包,还带一袋多出来的排骨,说是系统算重了,给我家多发。风一吹,塑料绳哗啦啦响,我心里“咯噔”一下,赶忙把箱子拖进屋檐下。抬眼一看,对门老郑家的窗帘半掩,屋里灯光暗,想到他透析后一直吃淡的,心一下就发软。 我没说啥,拿小刀割了绳子,排骨一股子冷气直冲出来,白花花的,冻得硬。我娘站在旁边,袖口挽到肘弯,手背上青筋一条一条,愣了半会儿,去找竹篮。我把柜子里存的藕和干香菇拎出来,热水壶也烧上,想着先焯一遍去腥。老爸在屋里咳了两声,把窗子开大一点,烟火味就从灶台那边往外爬。我心里也别别扭扭,既想留点自家过节,又觉得这东西压在脚边,像块石头。 最后干脆不拧了,拎着竹篮先送一半过去,再和社工打电话报错发。老郑家门口的台阶潮得发滑,他媳妇端着洗脸盆出来,面盆里浮着几片茄子。我把排骨递过去,嘴上就说做了多,不然放坏了可惜,顺便问问盐量咋把握。她眼圈红红的,又不肯多客套,只把门帘掀高一点让我别蹭着灰。我心里松口气,转头回家搭灶,铁锅上来就奔着大火,葱姜拍散,花椒在油里跳两下,空气像被打开的窗,吱地亮了。 灶台前热得人后背冒汗,我娘却不急,慢慢往锅里下藕块,手势稳当。排骨冒白沫,她用漏勺轻轻撇,动作像剪线头,利索又干净。院里小孩追着风跑,停在门槛那儿探头看,鼻子一抽一抽。我把旧铝盆翻出来,打了几小盆,盖上竹盖,用小推车拉到巷口的长凳上,给几个腿脚不利索的老邻居留着。风一会儿把香味推过去,一会儿又推回来,像顽皮的小孩,谁也不偏心。 快递小哥抄近道过来取退货,雨点正好落下,砸在他的头盔上噼里啪啦。他说系统要回收多发的礼包,我把空箱子递给他,人却让他先歇口气,塞了两盒热菜到他保温箱里。他手背裂着口子,贴了块创可贴,笑着摆摆手,说回头再吃不耽误。我看着他背影踩着水花跑远,心里那口气像是被锅盖捂住,呼的一下,热得更实了。院角的晾衣绳被雨打得滴水,老娘顺手多扯了两次,絮絮叨叨等会儿记得收。 夜里风顺了,雨停在瓦檐上,滴滴答答像有人数拍子。老爸坐在屋里捻烟丝,灯光把他的背影拉长,落在墙上安安静静。我娘在院子里拾葱叶,指甲缝被葱汁染成了浅绿,抬眼朝我笑了一下。我把做法发到村群,写得直来直去,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词儿,谁看谁会。手机“叮”一声,有人回了个大拇指,我没回,就把锅里的火再收小了点,想着等半夜再给边上两家各盛一碗。 第二天,老郑媳妇在群里说,昨晚他终于吃了两口有味儿的,血压没飙,睡得比前几天实。幼儿园的老师发了张照片,小朋友端着小碗笑,嘴角还挂着油星。合作社那边把多出来的礼盒折个价,记在我们名下,我算来算去,觉得这账不亏,心里反而落地。街坊从巷口过,远远冲院里摆下的空铝盆看了一眼,笑着摆摆手,像是知道个啥,又啥都不说。风从老槐树上掠下来,叶子“沙沙”响,我忽然想,这不就够了么。 晚上收拾碗筷,我娘把最后一块藕放进自己碗里,咬得慢,像是念叨。她不爱说大道理,最多念一句“别浪费”,就把话头砍断。我看着她背影,想起老爸那句老话,又觉得今天这点忙活,顶过一堆客套。灶台还温着,手掌贴过去暖烘烘,我把窗子关到只留一条缝,让香味留在屋里一会儿。这点热乎劲儿,难道不更顶用吗?
她的眼泪“该叫醒多少人”看到这张图鼻子一酸中国姑娘在破旧的茅草屋里抹眼泪孕
【51评论】【2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