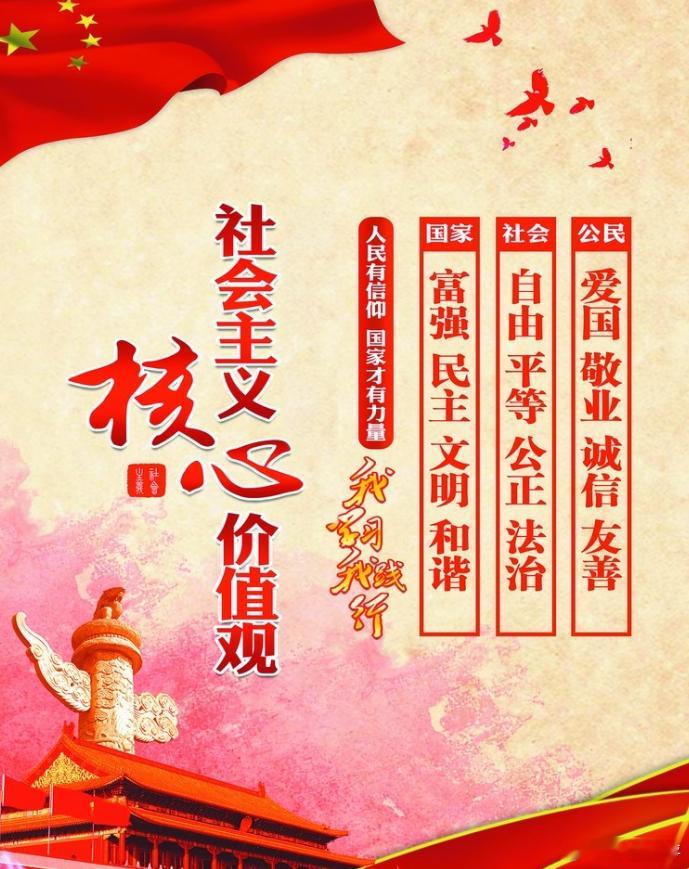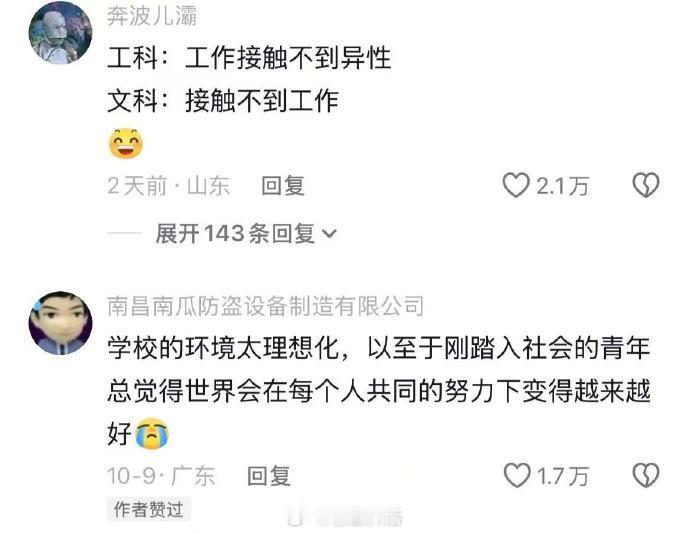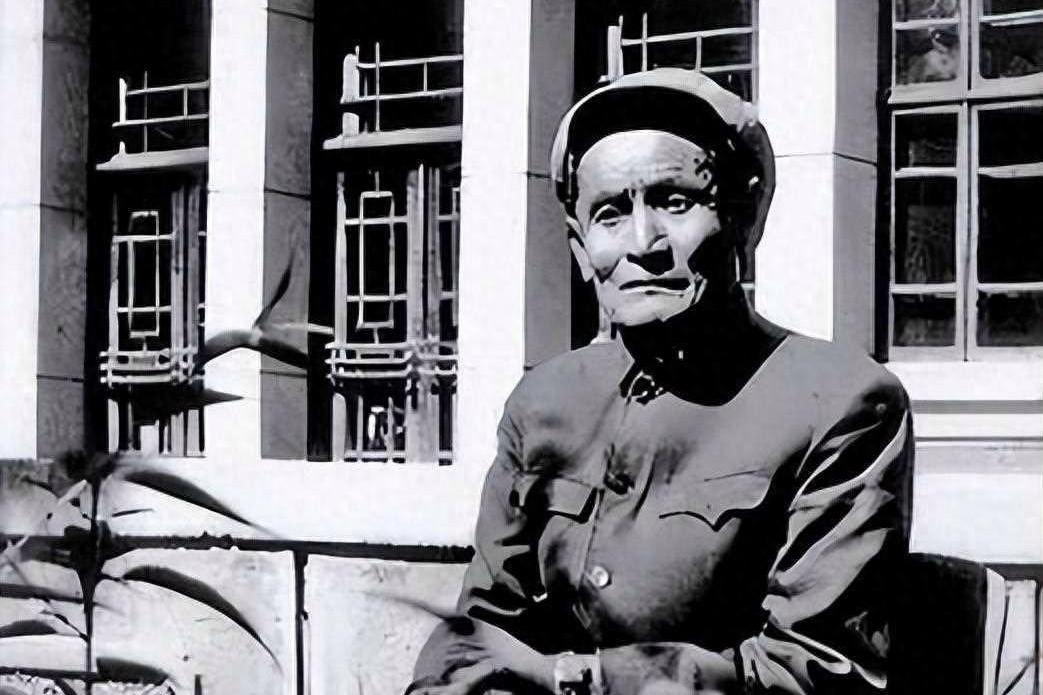【为啥有的罪犯被人们同情?孙玉良:用制度减少犯罪才是社会进步】
凡是罪犯都是“罪大恶极”,不值得同情与悲悯吗?关于如何对待犯罪与罪犯,社会始终存在着深刻的讨论。当罪恶发生时,公众的愤怒往往指向犯罪个体,要求严惩不贷。然而,上海开放大学教授、文化学者鲍鹏山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许多犯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惩罚个体来实现正义,更应追根溯源研究犯罪的原因,去推动社会现状的改变与制度缺陷的弥补。鲍鹏山的观点指出了一个关键命题:对个体命运的悲悯,最终必须转化为对制度完善的执着。用制度性力量系统性减少犯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推动社会进步。
对某些罪犯的悲悯与理解,并非为罪行开脱,也非对罪恶行为的姑息与原谅,更不是廉价的同情,而是通过一种理性的、深层次的追问,探寻犯罪根源。一个人,是如何从守法良民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是天生邪恶还是后天环境的挤压?许多犯罪,尤其是财产性、暴力型犯罪,背后往往潜藏着贫困的折磨、教育的缺失、社会不公的挫败感、阶层固化的绝望,或是心理健康支持体系的缺位。一个在健全制度、温暖环境中成长的人,与一个在破碎家庭、匮乏资源和暴力环境中挣扎的人,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有着天壤之别。理解这些社会性、制度性的“病因”,并非为罪犯卸责,而是为了更精准地诊断社会肌体本身的病症。这种悲悯,是对所有被社会结构性缺陷所伤害的个体——包括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一种人道主义关怀。
的确,从个体惩罚到制度疗愈,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必然转向。如果将犯罪简单归因于个人品德的败坏,并认为严刑峻法足以解决一切,那么社会将永远陷入“犯罪-惩罚-再犯罪”的循环。一个成熟、进步的社会,其治理智慧应体现在从热衷于事后惩戒,转向致力于事前预防。而对罪犯个体的悲悯与理解,正是这一转向的起点。当我们理解一个青年因缺乏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而参与盗窃,社会要做的就不仅是把他关进监狱,更要反思如何创造更公平的就业环境、提供更有效的职业教育。当我们看到一个悲剧源于长期的心理健康问题被忽视,我们就应大力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心理支持和干预体系。
有一个鲜明的例子被社会广泛关注,这就是有名的张扣扣案。张扣扣虽然被处死刑,但他在许多人心目中却是“英雄”,这不很值得人们深思吗?还有“前腐后继”的贪官污吏,难道只是个人品德问题?不能这么说吧。因此,我们要在制度层面上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犯罪,将“疗愈”社会的视角转向制度层面,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强化社会保障网,消除极端贫困,保障基本民生;促进教育公平与人格培养,让每个孩子都有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捍卫司法公正与社会公平,让每个人在制度中感受到被尊重和正义的存在;完善犯罪矫正与回归社会机制,降低再犯罪率,以及如何纠正腐朽的封建官场文化,让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真正地落实于公务员队伍中。
所有的这些,不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吗?一个“公正”的社会,意味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催生犯罪的不公;一个“法治”的社会,其法律不仅用于惩戒,更应该用于构建公平公正的秩序和社会保障权利。用悲悯之心,铸就制度之善。面对犯罪分子,我们不能只局限于愤怒与打击,而需要怀着悲悯之心去探索犯罪背后的复杂成因,并在找到原因后将其升华为一种强大的集体行动力,去修补制度的漏洞,去改善社会的土壤。构建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不是创造一个没有惩罚的世界,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犯罪率因制度完善而持续降低的社会。这需要执政者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需要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具备深刻的洞察力与坚定的决心,将对个体命运的关怀,熔铸于更坚固、更公平的制度堡垒之中。只有这样的思考,才是对社会进步最有力的诠释,也是对人民福祉最长久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