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北京永定门城楼因为“妨碍交通”被拆除。48年后,果不其然开始复建永定门城楼了,而复建过后的永定门被称为“北京城第一座复建的城门”。 大早上,在南城就响起了机械轰鸣声。 工人们挥舞着铁锤钢钎,砸在永定门城楼古老的砖石上。 这座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作为北京外城正南门、中轴线南端起点的巍峨建筑,在“妨碍交通”的判决下,正经历着最后“拆迁”。 永定门,取“永远安定”之意,是明世宗为加强京师防御、完善“凸”字形城廓格局而建。 它不仅是出入京畿的咽喉要道,更是北京中轴线这一城市规划杰作的南端起点, 清乾隆年间,城楼得以重修,更显规制宏阔。 它见证了明清两代的兴衰荣辱,亲历了外敌叩关的烽火硝烟,也默默守护着寻常百姓的市井烟火。 民国以降,古城墙与现代交通的矛盾初现端倪。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建设热潮席卷全国。 首都北京,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城市改造更是刻不容缓。 在“破旧立新”的时代洪流中,古老的城墙、城门被视为封建残余与城市发展的绊脚石。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部分文化界人士,更将古城墙视作旧中国积贫积弱、闭关锁国的象征,主张拆除以扫清现代化障碍。 然而,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首的一批有识之士,则选择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奔走呼号,力陈古城墙与城门的巨大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提出著名的“梁陈方案”。 保留老北京城,另辟西郊建设新行政中心。 梁思成视北京古城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是“历史的界碑”,拆除之举无异于自毁瑰宝。 然而,在“让路于发展”的压倒性共识下,梁林夫妇最终未能阻挡推土机的步伐。 1950年,永定门瓮城率先被拆。 1957年,城楼与箭楼也终告不保。 当永定门最后一块匾额被卸下时,林徽因忧愤交加。 梁思成目睹着自己倾力守护的古城肌理被一寸寸剥离,吐露了饱含悲愤与预见的断言:“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今日之谬!” 永定门的消失,只是北京古城墙系统性拆除的序幕。 此后数十年间,巍峨的城墙连同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在城市化浪潮中相继湮灭,仅余下正阳门城楼、箭楼及德胜门箭楼等零星孑遗。 北京城,完整的“凸”字形轮廓与壮丽的城门序列,就此成为绝响,只存在于老照片与老一辈人的记忆深处。 而当年梁思成的预言,并未被遗忘。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逐渐深化。 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同时,文化自觉开始苏醒。 那些消失的古城门,成为萦绕在北京人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符号。 进入21世纪,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城市形象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被提上重要议程。 如何展现古都风貌与现代活力的交融,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永定门这座曾扼守中轴线南大门的标志性建筑,其复建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它不再仅仅是一座城门的重建,更被视为一次文化记忆的修复,一次对历史欠账的弥补,一次向传统致敬的象征性回归。 2004年3月10日,距离1957年拆除整整四十七年后,永定门复建工程正式启动。 然而,工程面临巨大挑战! 因为,原始建筑已荡然无存,图纸资料亦不完整。 设计团队遍查明清档案、历史照片、文献记载,甚至远赴南京、西安等地考察同类明代城门遗构,力求最大程度还原其形制、结构与风貌。 复建严格遵循了历史原址,坐落在北京中轴线南端延长线上。 然而,复建终究是复建。 2004年国庆前夕,工程告竣。 崭新的永定门城楼拔地而起,重新屹立于南中轴线上,被官方冠以“北京城第一座复建的城门”之名。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楼庄严肃穆,吸引着市民游客驻足流连,拍照留念。 永定门的一拆一建,横跨近半个世纪,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拆除,是特定历史时期对现代化路径的单一理解与选择,是建设热情与文化认知局限共同作用的结果,留下了无可挽回的遗憾与梁思成锥心泣血的预言。 复建,则是时代进步、观念更新的产物,体现了社会对文化遗产价值重新审视后的尊重与珍视,是对历史记忆有意识的修复与传承。 城市的发展,并非只有“破旧立新”这一条路径,保护与传承同样是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维度。 新永定门的矗立,并非对拆除历史的否定,而是对梁思成等先驱者远见卓识的迟来致敬,是对“保护与发展并非非此即彼”这一理念的深刻印证。 永定门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也警示着未来。 真正的现代化,应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和谐共生,让历史的回响,成为照亮前路的明灯,而非湮灭于推土机下的尘埃。 主要信源:(北京市人民政府——永定门与广安门的风云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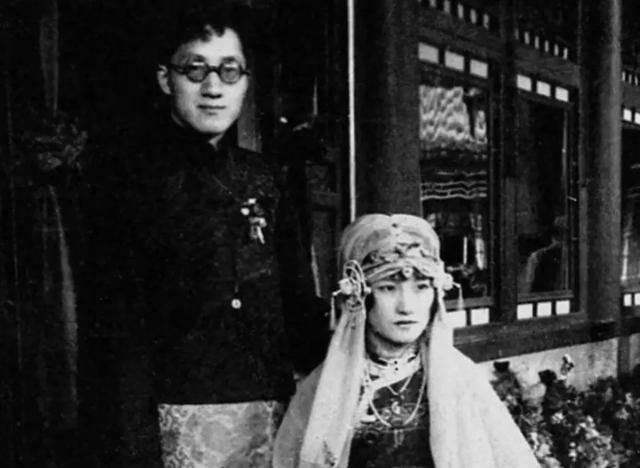


laoxi
希望成长的代价越小越好,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