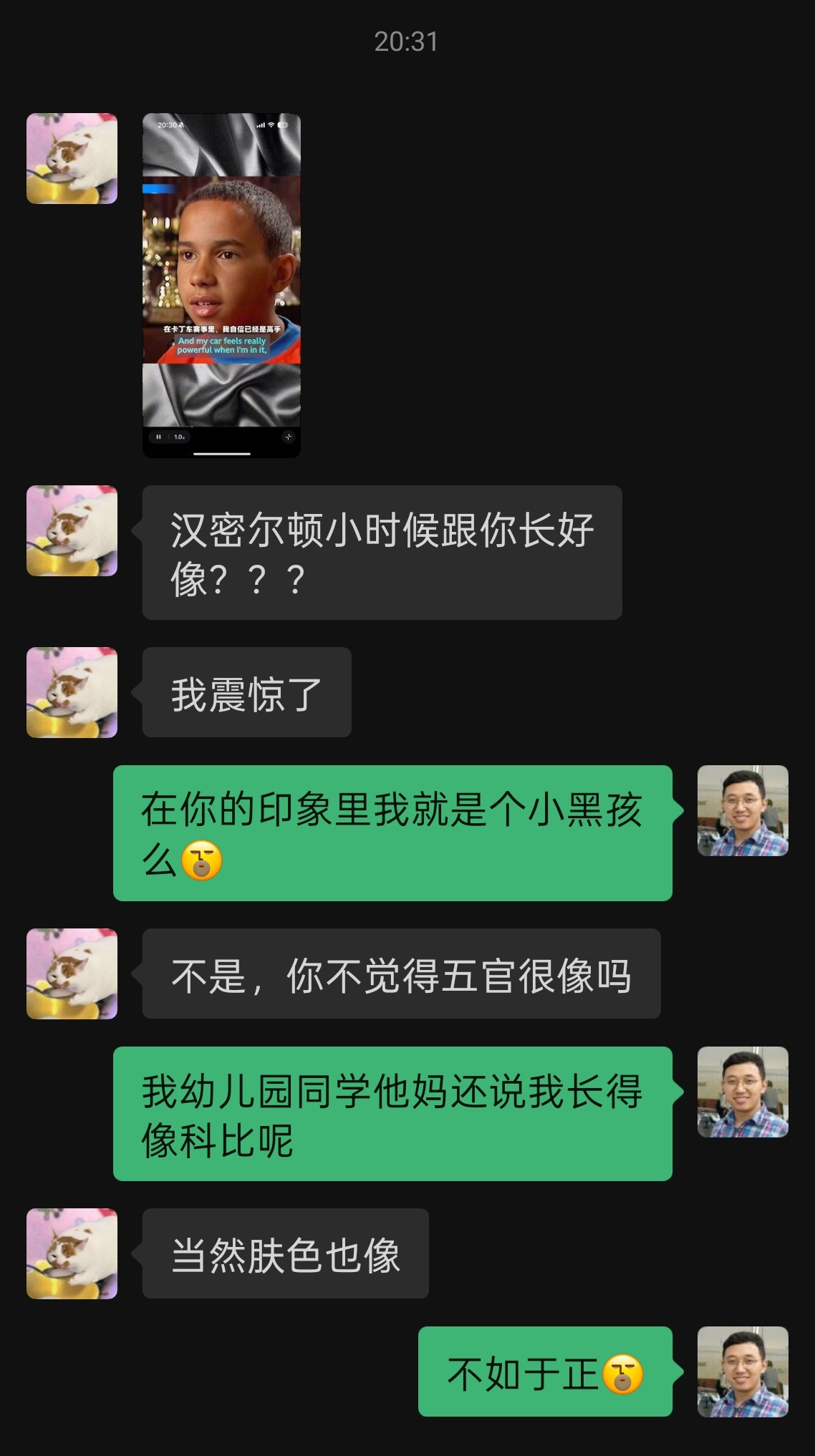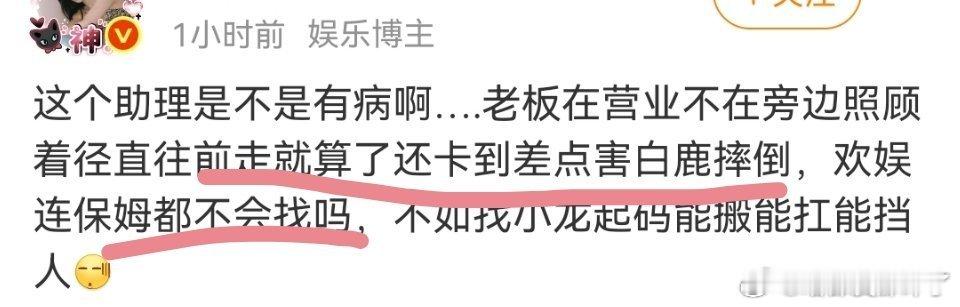母亲生了我们四个姑娘,我是老大。因为没有儿子,父亲在外面偷偷找了个小三,还生了个弟弟,此后父亲竟公然不回家,工资也不给我母亲,我们母女一家五口就靠母亲一个月三十几元的工资为生,那种艰苦的岁月就无法描述了。 我是家里老大,底下三个妹妹,母亲的肚子再没鼓起过带把儿的。 父亲的眉头就没松开过。他是厂里的钳工,扳手耍得溜,回家却总对着母亲叹气,“丫头片子,将来都是别人家的人”。 那年我八岁,母亲的工资袋磨出了洞,三十几块钱分角票卷成筒,塞在枕头下。每天清晨她数钱的声音比鸡叫还早,三分买酱油,五分打煤油,剩下的要攒着给我们交学费。 第一次见那个女人,是在巷子口的杂货铺。她牵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父亲拎着糖罐跟在后面,笑得我眼生疼。男孩穿的灯芯绒外套,是母亲想给我做却没舍得扯布的那种。 母亲那天没做饭。她坐在床沿,把我们四个丫头的脏衣服堆在膝盖上,针脚扎得又密又急,线头在指间绕成小结。我看见她手背的冻疮裂了,血珠渗进蓝布衫的补丁里。 “妈,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三妹拽着母亲的衣角问。母亲没回头,只把晾衣杆往高处举了举,“衣服得晒到太阳最毒的地方才不会发霉”。 后来父亲彻底不回了。工资单直接寄到那个女人手里,母亲去厂里找领导,人家拍着桌子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她回来时,裤脚沾着泥,手里攥着半块别人给的烤红薯,分给我们一人一小口,自己舔了舔手指。 有天夜里我起夜,看见母亲对着镜子拔白头发。煤油灯的光晃得她影子在墙上抖,她嘴里念叨着“再熬熬,丫头们大了就好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她掉眼泪,像屋檐水,一滴,又一滴,砸在脸盆里。 邻居王婶偷偷跟我说,“你爸也是苦,老太太临终前攥着他手,说‘老李家不能断了根’”。我摸着母亲纳的鞋底,针脚比父亲的扳手印还深,突然不懂,根到底是长在儿子身上,还是长在谁也不肯撒手的日子里? 母亲的工资袋后来换成了塑料的,还是磨破了角。她开始接零活,给人缝棉袄,一分钱钉十颗扣子。我们四个轮流帮她穿针线,妹妹的小手被针扎破了,母亲就把线头含在嘴里抿湿,“这样就滑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母亲的手肿得像馒头,却给我们每人缝了双棉鞋,鞋底纳着“平”“安”“喜”“乐”。我穿着带“平”字的鞋,踩在雪地里,听见咯吱咯吱的响,像极了母亲数钱的声音。 现在我也成了母亲,给女儿买进口奶粉时,总会想起母亲当年把玉米糊熬得稠稠的,往里面撒一把炒黄豆粉。她没说过爱,却把三十几块钱的工资,过成了我们四个丫头的春天。 那个磨破的塑料工资袋还在我抽屉里,里面没有钱,只有一张泛黄的纸条,是母亲的字迹:“丫头们,日子是熬出来的,熬着熬着,就甜了。”
我低估了中国网友对冷知识的执念。。
【1评论】【2点赞】